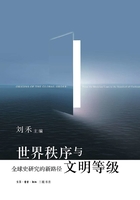
∷ 西学编译的政治
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等亚洲国家,在国际法的经典文明等级标准中被规定的位置是“半开化”国家。福泽谕吉是在认可日本的“半开化”地位的前提之下,提出他的“脱亚论”的主张。本书作者赵京华重新追溯福泽谕吉的思想谱系,重点考察了那个曾让福泽谕吉感到心悦诚服的“野蛮、半开化、文明”三段式论说。他的研究显示,福泽谕吉作为幕府使节团随员几次访问美国和欧洲途中(1860年、1862年和1864年),曾利用官府旅费购置大量的英文书籍。这批最早被他引入日本的西方著述中,含有大量的中学教科书,而福泽谕吉在编译《西洋事情》和《文明论概略》等书的过程中,依赖的主要就是这些通俗的中学教科书。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其实是直接摘抄福泽谕吉的文明发展三段式,包括其“富国强兵”的论述。因此,晚清人最早接触到的文明等级标准,除了传教士的出版物,一个重要渠道还是梁启超和福泽谕吉的编译文字。
在晚清中国,大量与“西学”有关的出版物都属于这样的“编译”文字。一旦迈过编译这个门槛,欧美国家的普通中学教科书和通俗出版物便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被冠以“西学”的名分,一时成风,朝野流行,受到维新人士的顶礼膜拜。本书郭双林的文章对晚清传教士与中国人编译的教科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他发掘的由晚清到民国的大量第一手文献都很能说明问题。很多当时欧美中学使用的历史地理教科书,正是通过编译的渠道进入中土,在向国人介绍历史地理和世界史知识的同时暗度陈仓,隐蔽地传播欧美文明等级的标准。其中,英美传教士的编译活动最为重要。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有时把英文原著直呼中国为half-civilized的真相加以遮蔽,有意让中国读者难以知情。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1885年编译的《佐治刍言》,就是这样一本初级教育水平的“西学”政治经济学课本。再如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万国公报》,也是宣传文明等级标准的重要推手,其影响至为关键。这些传教士的忠实读者中有一大批杰出的晚清维新人士,其中就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马君武等。
在传教士译介的欧美文明优劣的标准中,有一条被屡屡提及,那就是:“教化之地位,以女人之地位为衡”。想不到,这样一个有关文明教化的标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竟然引起严重的政治反应。本书宋少鹏撰文指出,妇女问题一跃而上升为晚清社会变革的核心议题,废缠足,倡女学,一时呼声高涨,不完全是因为维新人士忽然都拥护女权,深究起来,那是由于他们感受到来自欧美文明等级的沉重压力。文章中,她还把文明等级的标准形象地概括为“西洋镜”,指出晚清的维新人士就是在这个文明的魔镜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半文明”或“野蛮”的镜像,一边痛心疾首,一边又与之认同,所以,摆脱这个镜像才是他们出来倡导女学的真正动机。宋少鹏对邹容、梁启超、马君武等人著作的再诠释,还揭示了一个被长期遮蔽的问题——在晚清的富国强兵论述后面,藏有一个文明论的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基础,这突出表现在晚清知识界的一个共识中,即认为缠足的恶果在于它损害国民之母的身体,因而连带损害国民的整体素质;更严重的是,他们指责裹脚女子“不生利”“只分利”, 乃国民生计之大害,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逻辑上倡导女学的。
乃国民生计之大害,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逻辑上倡导女学的。
无论考察“西学”的产生和编译活动的关系,还是从文明“西洋镜”的角度重新观察近代话语的传播,这里不能不生出一个疑问: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这个问题经常被近代史的研究者所忽视,可是它至关重要。尽管晚清的士人不像日本精英那样主张“脱亚入欧”,但他们或是公开承认,或是默认了自己“半开化”的文明身份。这一点我们在郭双林和宋少鹏的研究中看得十分清楚。问题是,文明等级论不但在晚清和民国时代被人们普遍接受,它至今还驱动着人们的发展观,刺激着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想象。那么,文野之分如何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文明论与进步主义历史观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问世之时,进步主义历史观已大行其道,社会阶段论和文明等级论也已成常识。法国思想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的《现代欧洲的文明史》一书,出版在达尔文之前,不仅风靡欧洲,一时成为经典,而且影响至远。这本书为了对进步主义历史观进行系统表述,必然首先界定欧洲文明,而欧洲文明的界定又势必以非欧洲为限度,正如“我”必以“非我”为限度。那么,如何界定非欧洲文明?世界史写作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这里的循环逻辑是,世界史本身也是以欧洲设立的文明等级为大前提。程巍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对弘扬文明等级的世界史写作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的论述充分显示,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离不开文野之分,反倒是受到文明等级标准的制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这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推至顶峰。程巍提醒我们,黑格尔在19世纪初在柏林大学讲演历史哲学,秉承的恰恰是文明论的意识形态。当黑格尔阐释“世界精神”如何由蒙昧状态,抵达自觉意识,最终在德意志的大地上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他明确将中国放在了“半蒙昧、半文明”阶段。此外,语言文字的物质形态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他把中国的语言文字作为“半蒙昧、半文明”的证据之上。这不奇怪,因为语言进化论从来都是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反思文明论和进步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密切关联,程巍进而把晚清和民国废除汉字或汉字拼音化的诸种努力,也放在新的视野里进行观照和审视。总体来说,程巍的研究不但有效地阐释了语言进化论与文明等级论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对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如何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有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