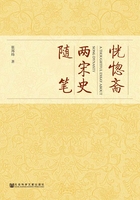
序跋
专题探讨、断代考察与综合研究
——《婚姻与社会·宋代》引言
本书将采用把宋代同以唐代为主的前代相对比的办法,对唐宋之际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和婚姻观念的某些变化做些介绍和探讨,试图借以显示唐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更深一层地认识宋代社会。当然,这只不过是心向往之而已。
不必讳言,把人类文明史等同于阶级斗争史、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唯物论的狭隘理解,曾经使史学领域出现过内容单调、选题重复的弊病。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狭隘理解早已成为过去。如今,历史研究者们几乎无不深切地感到,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内容,是个极其复杂的、立体式的组合,对它进行单打一的考察无济于事,必须致力于多角度、全方位的整体性探讨。眼下日渐趋于活跃的社会史研究,正是研究者们为了振衰起弊,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所做的一种重要努力。
婚姻作为人类的自身生产,与人类的物质生产一道,构成了社会生产的总体,并对整个社会起制约作用。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有“微型社会”之称,而婚姻又是家庭产生的基础。婚姻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件“终身大事”,并且在人际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素来被称为“人伦之首”。可见,婚姻本来就是社会史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显然也应当属于整体性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向来十分重视婚姻问题的研究。是他们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并用自己的出色研究成果如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学奠定了坚固的基石。这些著作对于婚姻史研究,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这一学术领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上的“不完全遗传”所致,以至于今天不得不旧事重提。
就中国古代婚姻史而言,尽管研究基础相当薄弱,但绝非前无古人。远的且不去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吕思勉、陈顾远等人就对此进行过具有开创意义的专门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当然,他们的著作如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小史》[1]、陈顾远《中国婚姻史》[2],在事隔数十年之后,已经显得观点较陈旧、内容欠充实,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史”的特点不够鲜明,便是吕思勉、陈顾远等人的婚姻史著作的一个共同缺陷。陈顾远在其《中国婚姻史》一书的序言里讲得很明白,他采用的是“纵断为史之法”。该书不是按时代、分阶段进行论述,而是按问题分门别类介绍。人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婚姻制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的前后演变,不免要怀疑它是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史”。何以如此?这固然与婚姻制度具有稳定性相关。可是,稳定性与变异性并非冰炭不同炉。所谓稳定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义语,它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无非是指演进的节奏较缓慢罢了。美国知名学者摩尔根说得好:婚姻家庭形式“必须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3]。古代中国毫无例外,婚姻制度有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可寻。
在研究基础尚薄弱的条件下,目前就贸然着手编写一部较完善的大型《中国古代婚姻史》,似乎有些脱离实际,并不怎么现实。当务之急恐怕是: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们群策群力,先分头做一些专题探讨、断代考察,为从总体上进行综合性的再研究打下基础。本书的撰写,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之所以选择宋代作为课题,除受笔者的知识结构局限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鉴于从前对宋代婚姻制度探讨较少。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婚姻史的研究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就民族而言,少数民族婚姻史研究“热”一些,汉族婚姻史研究较冷落。从时代上说,五代以前还有些成果,两宋以后就寂寂寥寥了。这一状况固然事出有因:越是处于社会发展的较低级阶段,婚姻对社会的制约作用越明显,因而也就越受到人们的注视。但是,似乎还可以这样说:越是处于社会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婚姻问题越复杂、内容越丰富,现实意义也越大,因此也就越值得研究。这里不打算讨论上述两种说法的是非曲直、高低长短,只是试图说明: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者都不应当把它排斥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
二是因为探讨这一课题有助于加深对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认识。婚姻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一张相互贯通、相互牵制的网络。婚姻既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制约作用,又受社会风尚影响、为政治制度所制约,并最终被经济结构决定。一言以蔽之:“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4]既然如此,那么探讨封建婚姻制度发展到宋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呈现出什么新特色,势必能够从一个重要方面综合地体现和反映唐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唐宋之际到底有无社会变革?如果有,其性质又如何?眼下,国内外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还有不同认识。单就国内的唐宋社会变革论者而言,又有“停滞论”与“发展论”之分。有的断言,这场变革意味着从发展到停滞,有的则认为,这场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有鉴于此,从婚姻的角度对此做些考察,仿佛不算多余。
三是由于探讨这一课题有可能给予今天的人们某些历史的启示。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历史学的目的就是使各民族和人类认识自己。”[5]这话不无一定道理。我们民族的婚姻传统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优根和劣根、长处和短处?这类问题的答案应当从历史中去寻求。本书将对我们民族的婚姻传统做些历史考察,并结合相关史实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这或许也并非可有可无。
最后需要说明,本书并不是一部宋代婚姻史,它远远未能穷其细节、俱其始末。即使对于宋代婚姻制度所应当包含的全部内容,本书也还没有做到囊括无余。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笔者对它们还若明若暗,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有的则因为笔者认为它们无关宏旨,不必凡事必录。有学者担心: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会不会使历史变得十分琐碎?这种担心多半属于误解。其实,所谓开拓研究领域,并不是漫无边际,细大不捐,凡事必究。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不过,这种担心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它相当及时地提醒我们:即使从事社会史研究,也应当着重考察那些具有社会意义、能够反映本质的历史现象,并尽可能地揭示其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本小册子正是抱着上述想法,力图把问题放到纵的历史过程和横的历史联系中去探索,尤其着力于前后对照抓特色。不过,俗话说得对:“说则容易做则难。”究竟做得如何,留待读者去评判。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 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上海中山书店,1929。
[2]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6。
[3] 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第492页。
[4] 摩尔根:《古代社会》,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9页。
[5]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4册,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9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