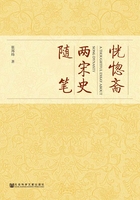
史事尤应全面看
——关于当前宋史研究的一点浅见
近40年来,宋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常言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尽人皆知:良好的评论机制是学术进步的动力。21世纪初,包伟民等一批宋史学者力图掀起一股自我质疑、集体反思之风,有《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1]一书问世。虽然引起重视,风声还算较大,但雨点似乎较小。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积习难改,有的学者近年依旧感叹:“学术评论之难”,“许多学人不愿意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2]。愚见以为,当今宋史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主观片面性便是其中之一。问题虽属浅层次,但不可小视,最难防避。前辈史家翦伯赞生前所著《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且针对性极强。《初步意见》一文几乎通篇讲的都是如何避免片面性、防止简单化。翦老强调:“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3]。当今宋史研究中主观片面性的主要表现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下面仅粗略举些实例。
其一,各走极端。宋代“积贫积弱”论与“理想社会”说、士大夫“高尚”论与“龌龊”说、富民一概“为富不仁”论与“社会中坚力量”说,看似针尖对麦芒,其实都是各执一端的偏颇之论。总体上说,宋代士大夫既非纯属一堆肮脏龌龊的粪土,亦非个个都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笔者尤其不赞成宋代“富民是主要纳税人”一说。众所周知,传统时代的分配体制是:佃户交租,田主完粮,粮从租出,租为粮本。田赋分明是地租的分割,田赋来自地租。不能把劳苦大众排除在外,片面地将富民视为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翦伯赞当年告诫我等:“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而今我们怎能见士大夫就反,见富民就骂?反之,也不能见士大夫就赞,见富民就捧吧!这些,笔者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4]等文中曾言及,这里不再多说。为了表达对宋代农民欢乐说的不认同,我曾较多引用钱锺书《宋诗选注》(以下简称《选注》)中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诸如《前催租行》《后催租行》等,于是被视为宋代农民苦难论者。《选注》编写于20世纪50年代,受到时代与体例双重局限。如今我们肯定可以从72册之巨的《全宋诗》中找出若干反映农民欢乐的诗篇,而且数量不会太少。然而宋代农民绝非时时欢乐、人人欢乐。丰年多欢乐,灾年很痛苦;形势户、上户欢乐多,下户、客户苦难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前代相比,宋代农民生活确有改善。但对宋代农村不能理想化,绝非处处充满欢声笑语的美好田园。宋人程颐有句惊人之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致从前人们普遍将宋代视为妇女社会地位急转直下的时代。笔者30多年前撰有《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5]一文,认为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于唐代,旨在说明宋代妇女社会地位处于下降的过程之中,而非急转直下。或许与此有关,于是出现宋代妇女幸福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宋代妇女再嫁多,显然不能引以为据。传统时代,妇女另嫁绝非幸福,往往悲痛欲绝。听听宋代一位“弃妇”对亏心汉的声讨:“功名成遂不还乡,石作心肠,铁作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荣光。”[6]那位为赋税所逼而被迫改嫁的老妇,更是“行行啼路隅”,“欲死无刑诛”[7]。我当年将妇女再嫁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一并讨论,虽然事出有因,现在看来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二,只知其一。任何社会都是个复合性的整体,总是死的抓住活的,新的旧的同在,多种现象并存。我早年所著《试论北宋“婚姻不问阀阅”》[8]一文就存在看问题较片面、阐述欠充分的问题,陶晋生在《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一书中列举出若干反证[9],值得参考。特别应当注意,阀阅与门第不是一个概念,不问阀阅与门当户对并非绝对对立。婚姻不问阀阅虽然属于新事物,尤其值得重视,但不能无视门当户对这一旧习俗的存在。婚姻不问阀阅又论什么?强调婚姻“论才”者有之,主张婚姻“论财”者亦有之。全面地看,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宋代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的“榜下择婿”之风颇为盛行,其表象是“论才”,其实质是“尚官”,表明社会心理由“尚姓”即“崇尚阀阅”转向“尚官”即“崇尚官爵”。婚姻“论财”由来已久,宋代自有其新特点。从前卖婚者非门阀士族莫属,宋代则以新科进士为主。婚姻“论财”与婚姻“论才”,表象不同,实质一致,两者都是新的门当户对观念的体现,具体而生动地显示了唐宋之际社会历史演进变迁的轨迹。又如在元朝攻灭南宋时,士大夫分道扬镳,既有归降者,也有不降者。有学者为证明宋代士大夫肮脏龌龊,忽视后者,强调前者,断定士大夫大多归降元朝。其依据是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10]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其反证不少。《宋史·忠义传一》序就说:“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11]元史学者陈得芝的统计较为确实: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12]士大夫大多归降元朝一说,其片面性显而易见。
其三,过甚其词。宋代士大夫敢于说话,有“论建多而成效少”[13]之称。在他们连篇累牍的言论中,渲染之词颇多。渲染虽然能收到引人注目的效果,但一渲染就失真。如北宋大臣夏竦“恐不数十年间,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14]一语,用以说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尚可,以此证明宋代商人数量即将超过农民则非。自号“安乐先生”的北宋名儒邵雍不厌其烦地声称“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15]邵雍所说只是其自身感受,具有极大的主观片面性。众所周知,北宋内忧外患不断,绝非“太平无事”的“全盛时”。这类夸张的话语显然不能作为宋代是什么“理想社会”“黄金时代”的依据。某些宋史研究或许受宋代士大夫潜移默化,夸张离谱的论断与结论时有所见。有的外国学者断言:“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16]读者在惊讶之余,不免怀疑译文是否有误。有的本土学者居然也如此认为:“唐宋之间,是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17]又如称南宋为“海洋帝国”。南宋海外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南宋,堪称不刊之论。然而依我之见,岂止南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足以号称海洋帝国。至于南宋,即使称为“半海洋帝国”,只怕也相当勉强。
其四,数据离谱。就论证方法来说,以数据为证无疑胜过试举例以说明之。但宋人提供的数据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宋代军费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高,毋庸置疑[18]。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蔡襄、张载、陈襄都是北宋中期人,年纪相若。这三位同时代人,便其说不一。蔡襄称:“养兵之费常居六七。”[19]张载言:“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0]陈襄云:“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1]到底相信谁的?照我看来,都是“估计参谋”。人们固然有理由认为,蔡襄曾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所言可信度应当很高。但他在治平元年,除“养兵之费常居六七”一说之外,还另有一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22]六分之五,即十分之八强。一年之中,两个不同的数字居然出自蔡襄一人之口。关于北宋开封的人口,种师道称“京师数百万众”[23],已经相当夸张。刘攽说得更悬乎:“京师至三百万家。”[24]以一家五口计,北宋开封一城人口竟达1500万人之多,即令包括开封府所辖16县在内,也让人无法想象[25]。但我当年居然在《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26]一文中引以为证。过后方知:上当。至于“京师亿万之口”[27]、东京“居者无虑万万计”[28]云云,纯属天方夜谭。《宋史·食货志·农田》载:治平年间“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29]。去掉余数,以3000万顷计,再按一宋亩等于0.865市亩换算,当时天下垦田多达25.95亿亩,大大超过现今全国耕地总面积。人们难免会问:这可能么?有位前辈学者早年信以为真,据此记述道:“到英宗时,全国耕地共三千多万顷。”[30]好在20世纪50年代初杨志玖著有《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文,专门予以订正[31]。后来,何炳棣在《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史籍有关北宋垦田面积的记载“决不会反映当时的耕地面积”[32]。这些教训理当吸取,然而当前在某些著述中,这类离谱数字仍时有所见。如宋代城市化程度很高,“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宋代农业生产率很高,“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发达地区“为6930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这些有悖常理的数字,据说是计算出来的,但终究很难令人信服。“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包拯年薪超千万,富可敌州。”[33]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主要是在网络与媒体上流传。正式出版的著作《两宋风云》竟然也列举出一些离奇数字:“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34]作者不屑于注明出处,让人高深莫测,不知其依据何在[35]。
由上所述可见,强调失度、主观片面、过甚其词、数据离谱,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缺少说服力。问题在于:主观片面性为何较为常见?只怕与以下两种因素关系极大。
一是绝对对立的思维定式。如在宋代的皇权与相权的探讨中,一方坚持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断言宰相“有如羊一样顺从天子”[36];另一方力主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认为宋代处于君主立宪的前夜。两种说法截然相反,但其思维方式惊人的一致,都立足于皇权与相权绝对对立,只能此强彼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俗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称为“在绝对不兼容的对立中思维”。[37]皇权和相权绝非两种平行的权力,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不是绝对对立,并非此强彼必弱[38]。又如学人研究唐宋变革,往往采用对比法,笔者即是一例。拙著《婚姻与社会·宋代》开篇就说:“本书将采取把宋代同以唐代为主的前代相对比的方法”,“试图借以唐宋之际历史运动的轨迹”[39]。唐宋两代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前后连续。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正如邓小南、荣新江所说:唐宋两代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又具有“连续性”,唐宋时代是“延续与更革”两者并存的时代。[40]用对比法研究唐宋变革,其长处在于凸显更革,其弊端则是忽略延续,片面性较大,容易割断历史。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漫长渐变过程,很难一刀两断。宋代的种种新事物、新现象大抵兴于唐、盛于宋,并非全新。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的解体以及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等,都发生在中唐前后,只是在宋代定型而已。我曾将对比法广为运用于对比唐宋学校、唐宋妇女、唐宋宗室以及后妃、公主、驸马、外戚、宦官。而今反思,对比法不甚可取,宜用过程论。
二是先入为主的惰性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历史是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宜一概否定“理论预设”和“目的取向”。研究者阅读相当数量的史料之后,必然从中抽象出一些有益的假设。关键在于不能先入为主,把假设当定论,再有选择性地去搜罗史料,对反证则置若罔闻。而应当将初步抽象出来的假设再客观地回到更多的史料中去验证,以充实、修正乃至放弃起初的假设。我不赞成“宋代仍处于庄园农奴制阶段”一说,曾经主张“凡宋代庄园皆行租佃制”。这个“皆”字显然不准确,太绝对。朱瑞熙等对此提出批评[41],理当虚心接受。其实我的文章中就有夔州路地区的反证,究其原因则在于先入为主,忽视反证。我曾自称“较为固执的唐宋变革论者”,特别关注宋代不同于唐代之处。日本学者荒木敏一认为“读书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宋太祖统治时期[42],这引起我的重视。于是我也热衷于寻找宋代的首创,诸如殿试、覆试、别试、糊名等。过后方知,“读书人”一词之类并非首见于宋代。李渊曾怒斥李德林“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43],见于《隋书》。宋代读书人只是数量增多,地位明显提高而已。宋人富弼说:“至唐武后,始有殿试。”[44]殿试系武则天首创,此后偶或为之。宋太祖时,“殿试遂为常制”[45],制度化、常态化了。宋代殿试与唐代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省试之外,再有殿试”[46]。至于糊名考校,一说始于唐初,武则天时废止[47];一说系武则天首创[48],后来缺乏连续性。唐代糊名仅限于铨试及制举,宋代从太宗开始,逐渐推广到一切科举考试[49],乃至武举。宋人高承概而言之:“糊名考校,自唐始也。”[50]此言虽不算精准,但大体属实。此外,如覆试、别试[51]以及“榜下择婿”之类,其源头均应追溯到唐代,宋代无非更盛行而已。寻找第一,无可厚非,但应尊重历史,不可轻言首创。
本文重在自我反思,并无多少新意,其要点无非两句大实话:多些全局观,少些片面性;不能见风就是雨,捡起封皮就当信。翦伯赞说得好:“历史家不是诗人”,“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一叶惊秋’是诗人的敏感,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少要多看见几片树叶,才能说秋天到了”。我等不应以“语不惊人誓不休”为目标,当以“文章不写一句空”为追求。愿与同道共勉:“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 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
[2] 彭卫:《近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观感》,《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3]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又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两者个别文字稍有差异。以下凡引翦老语,皆出自此文。
[4]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 张邦炜:《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后收入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第149~180页。
[6] 李有:《古杭杂记》,陶宗仪:《说郛》卷4,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34页。
[7] 李觏:《哀老妇》,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348《李觏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4294页。
[8] 张邦炜:《试论北宋“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后收入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第39~61页。
[9]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第4章“士族的婚姻”,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1,第101~135页。
[10]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醉歌》,孔凡礼辑校,中华书局,1984,第16页。
[11] 脱脱等:《宋史》卷446《忠义传一》,中华书局,1977,第13149页。
[12] 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第571~595页。
[13] 脱脱等:《宋史》附录《进宋史表》,中华书局,1977,第14255页。
[14] 夏竦:《贱商贾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45《夏竦十三》,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52页。
[15] 邵雍:《伊川击壤集》,卷10《插花吟》、卷5《秋日登崇德阁二首》、卷17《观棋小吟》,陈明点校,学林出版社,2003,第126、46、230页。
[16]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1页。
[17] 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5页。王曾瑜认为:唐宋时代“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页)。他的估计或许偏低。
[18]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第395~402页;王育济《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19] 蔡襄:《论兵十事奏(治平元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003《蔡襄十》,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84页。
[20] 《张载集·文集佚存·边议》,中华书局,1978,第358页。
[21] 陈襄:《上神宗论冗兵》,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1《兵门·兵议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330页。此文文末原注:“熙宁二年上,时知谏院”(第1330页)。
[22] 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强兵》,《宋朝诸臣奏议》卷148《总议门·总议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694页。此文文末原注:“治平元年上,时为三司使”(第1696页)。
[2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0“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丙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25页。
[24] 刘攽:《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503《刘攽二十》,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84页。
[25] 据《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畿路》记载,开封府所辖16县为开封、祥符、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阳武、延津(旧称酸枣县)、长垣(曾称鹤丘县)、东明、扶沟、鄢陵、考城、太康、咸平。崇宁年间,开封府“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第2106~2107页)。以一户五口计,总人口超过110万。此时,北宋开封已是上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应无疑义。周宝珠教授的估计是:“北宋东京最盛时有户13.7万左右,人150万左右”(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325页)。
[26] 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连载。
[27] 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状》,《宋朝诸臣奏议》卷106《财赋门·荒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144页。
[28] 宗泽:《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靖康元年九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第16页。
[29] 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中华书局,1977,第4166页。
[30]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光华书店,1949,第447页。吕老《简明中国通史》撰写于1947年,当时身处战争前线,查找史料之难,异乎寻常,出此差错,在所难免。
[31] 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
[32]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9页。
[33] 参见新华《“包青天”年薪过千万》,《江南时报》2011年2月21日,第14版。
[34] 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35] 参见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
[36]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第19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1页。
[38] 参见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后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1~21页。
[39]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页。
[40] 邓小南、荣新江:《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序》,邓小南、荣新江执行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41] 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184、190页。
[42] 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69。转引自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公司,1980,第35页。
[43] 魏徵等:《隋书》卷42《李德林传》,中华书局,1973,第1199页。
[44]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中华书局,1977,第3613页。
[45] 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中华书局,1977,第3606页。
[4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举士》,中华书局,1986,第272页。
[47] 髙承《事物纪原》卷3《封弥》:“封弥即糊名也,唐初以试有官人”(金圆等点校,中华书局,1989,第167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中华书局,1975,第1175页)。
[48] 刘昫等《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传中·刘宪传》:“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中华书局,1975,第5016页)。刘 《隋唐嘉话》卷下:“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1997,第35页)。
《隋唐嘉话》卷下:“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1997,第35页)。
[49] 参见徐规、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50] 髙承:《事物纪原》卷3《封弥》,中华书局,1989,第167页。
[51] 参见魏明孔《唐代科场作弊及其防范措施述论》,田澍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第205~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