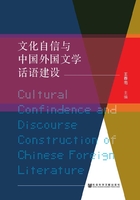
宏观文学现象研究
文学中的18世纪英国
刘意青
文学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但这在后现代文学追求魔幻、科幻、意识流、超现实等各种尝试的今天,要从文学中看社会就远不如18、19世纪直接和真切。18世纪后半叶兴起和首次繁荣的英国现代小说因此是我们了解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宗教、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我国自1949年以来长期忽视18世纪英国,对该世纪的英国文学了解远不如对之前16~17世纪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或之后19~20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维多利亚小说以及伍尔夫和乔伊斯引领的意识流作品。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又紧追后现代的各种新潮流,就更少关注18世纪英国这个与中国当前商品经济大发展十分有相关性的社会阶段和它的诸多思想家和文学成果。因此,这篇文章想通过当时英国的几位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所展示的18世纪英国的状况,为我们认识西方,特别是英、美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基和来龙去脉提供一点参照。
历史背景简介
17世纪至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即清教革命(1647~1649)也是英国唯一一次的流血革命,其后英国上上下下都努力避免流血斗争,采取了改良政策。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经历了几番和平的政权更迭。①借资产阶级革命上台的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以1660年议会迎回查理二世的王权复辟为终结。②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人,弟弟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统治激怒了国人,于是议会从荷兰迎回了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女儿玛丽和她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共同执政,史称这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初步建立了以托利(即当今的保守党前身)和辉格(即当今的工党前身)这两党为基础的内阁体制。而被驱逐的詹姆士二世逃亡苏格兰,他的支持者被称为詹姆士党人(Jacobites),他们不断从苏格兰入境骚扰,造成18世纪早期社会的不安定。与詹姆士二世余党的小规模战斗和议会两党的斗争在菲尔丁、笛福等人的小说里都有所反映。③玛丽无子女,她死后议会拥戴她妹妹安妮为女王(1707~1714在位)。④安妮仍无子女,她过世后议会只好从德国引进汉诺威家族的乔治[1],史称乔治一世(1714~1727在位)。从此时起英国终于建立起议会为主的君主立宪制,议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权机构,英国就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发展阶段。
文学中的18世纪英国
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农村土地贵族逐渐衰落,以伦敦为首的大都市慢慢成形。蒸汽机带动的工业革命,以及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洛克为首的社会科学大发展,使得英国很快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到了18世纪中期印刷术的普及造就了城市中繁荣的图书市场,价廉的各种书刊热闹非凡。于是作家们不再依赖权贵的恩准和扶持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读者也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扩大到中下层百姓,其中包括想要进步和提高自身文化的仆女、店员和徒工。图书市场上销售的不仅是严肃和需要高等文化素养才能撰写的诗歌和戏剧,更有各类普及型的散文作品,如游记、日志、历史、传记、神怪故事、各种尺牍书和行为指南,不一而足。这些散文作品和各种期刊大大助推了18世纪中后期现代英国小说的诞生,而且也铺垫了女人舞文弄墨的道路,以至于到18世纪中后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小说首次繁荣。[2]在这个英国小说繁荣的大潮中,不仅出现了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理查逊、斯特恩、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这些男作家,还涌现出一批以范尼·伯尼为首的优秀的女作家。更令人叹服的是,所有这些小说家都以教育大众为己任。虽然有写作挣钱糊口之需,但每个作家都积极投身时代潮流,从自己的角度写出反映社会问题和警示大众的作品来。比如斯威夫特揭露讽刺两党政治的荒唐,英国对爱尔兰的残酷剥削,以及当时的宗教分歧和斗争;笛福主要宣传不畏艰难困苦,自我奋斗的上升资产阶级价值观;菲尔丁则抨击虚伪、势利、奸诈,宣扬做人要善良、正直和富有同情心;而理查逊和伯尼等女作家则描写年轻女孩子的成长,警告她们躲避婚恋陷阱,洁身自爱。下面就从4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作家如何在他们的小说中反映当时英国的社会、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
1.反映宗教分歧和斗争、两党斗争以及批评时政的作品
首先要谈及的是18世纪的宗教分歧。众所周知,英国从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建立了信仰新教(Protestantism)的英国国教会(又称安纳甘教会)之时起,英国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的管辖,国王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首领。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天主教就成为英国最大的宗教敌人,天主教徒到处受到歧视,如著名诗人蒲柏的早年遭遇。王权更迭也常与国王本人不信仰国教有关,如詹姆士二世被逐。而信仰天主教的邻国法国又因宗教原因不断介入英国政治,支持天主教力量,造成两国长期不睦。然而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中小资产阶级逐渐壮大,出现了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教派,称为清教(Puritanism),并于1647~1649年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反对封建贵族和上层资产者以及代表他们的英国国教教会,提倡勤俭持家,个人奋斗,劳动致富,并节制欲望,反对教会的铺张浪费和繁文缛节,以及对教民的控制,主张通过个人反省赎罪来获得上帝的圣恩。但在王权复辟后,他们被称为反对国教的宗教异见者(dissenters),在英国受到迫害,比如弥尔顿和班扬。实际上,英国的很多政治斗争都与宗教斗争纠缠在一起,而文学也就成为反映和介入这一斗争的场所。
18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毕业于三一学院,之后进入国教教会奉职。虽然他代表英国国教教会到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爱尔兰任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持,但是他能超越宗教羁绊,写了不少抨击英国盘剥爱尔兰人民的名篇,为爱尔兰百姓伸张正义,得到爱尔兰人民的拥戴。他垂芳千古的讽刺佳作《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作为一个国教牧师,特别在他还没有认真介入爱尔兰事务之前,他也积极地参与了热闹的宗教论战。《一只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1704)就是这样一部论战作品,一部讽刺佳作。书名来自水手航海时经常抛出一只木桶把接近航船的鲸鱼引开,免得撞船。1651年霍布斯发表了主张集权,反对教会分权的著作《利维坦》,该词的英文意思就是巨大的怪物或鲸鱼。斯威夫特用了这个题目把自己的故事比作水手抛出的木桶,要引开霍布斯这类人对教会的攻击。整部作品引经据典,充满论证,但其中心是一个寓言故事。故事中,一位老人临死前给三个儿子各留下一件同样的外衣,并叮嘱他们不准做任何改动。然而,日子久了,老大彼得(代表罗马天主教)就在外衣上加缀了许多装饰,并镶上金边,搞得不伦不类。小儿子杰克(代表加尔文和清教)则把外衣的袖子和下摆任意剪短,弄得面目全非。只有二儿子马丁(代表马丁·路德和英国国教会)没有对衣服做任何改动。由于意见分歧,在整个改,还是不改外衣的过程中三个儿子争执不休,直至吵翻。此争辩过程展示了斯威夫特的国教立场,但仔细阅读仍会发现,作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作者在书中讽刺的不仅是天主教教会和清教,他也大量抨击了包括国教在内的教会这个体制和诸多行为,流露了对宗教的一些怀疑态度。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出身中小商人家庭,因信仰清教而只能在给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孩子专门设立的学校接受初级教育,因此他基本是自学成才。但是他的清教立场十分坚定。1702年他发表了一篇讽刺托利党人迫害清教徒的文章,叫作《对待非国教徒的最简便办法》(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建议将清教徒们赶出英国,将清教教士处以绞刑,犀利地讽刺了当权的国教教会对不同教派的打压。但是他假充托利党人的口气如此的逼真,所以刚开始主张迫害清教徒的托利党人还愚蠢地为他叫好,比较温和的辉格党人则十分愤怒。等到官方缓过神来,笛福就被抓捕入狱,还罚他在市中心枷示三天。笛福勇敢地面对迫害,当场写了一首《颂站枷》(Hymn to the Pillory,1703)并当众朗读,被伦敦市民奉为英雄。笛福一生政治无立场,常被后世人诟病。但他的清教立场始终坚定。他还出版了一本指导年轻姑娘婚恋的小册子,叫作《教徒的婚恋》(Religious Courtship),宣传姑娘们一定不能嫁给天主教徒和国教徒,只有嫁给清教徒婚姻才能美满幸福。可见当时宗教斗争渗入了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立场,它直接影响了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
除了宗教分歧,18世纪英国的两党斗争十分激烈。光荣革命后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在位时是托利党领导议会,通过了《权力法案》初步肯定了君主立宪体制,并为了争夺海外霸权而不断与法国和西班牙交战,获胜后的英国则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力量。然而,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加剧了国内债务负担,资产阶级便成为埋单人,而议会,特别下议院,对国内外事务的投票权就牵扯到了各方的利益。于是,两党争权夺利到18世纪上半叶就逐渐白热化。为了竞选,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和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辉格党各有自己的报刊,并雇用了许多写手撰文相互攻击。托利党之后,辉格党党魁沃波尔上台,他在执政期内通过了多个法案,包括试图确保辉格党在上议院的永久霸权的《贵族法案》,以清除武装部队和政府各级机构中的托利党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18世纪的两党矛盾,也让沃波尔本人成为众矢之的,在18世纪文学作品和漫画中变成了嘲讽和攻击的目标。[3]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人作家很多都有党派。比如斯威夫特,他先追随他的亲戚邓波尔加入了辉格党,后因辉格党不支持他在爱尔兰的教会事业而转入了托利党,交结了托利党文人蒲柏和盖伊等好友,并为该党编写党报《考察者》。但是斯威夫特的党派立场并没有影响他把讽刺的矛头指向英国两党制的肮脏与荒诞。在他著名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的第一卷中,斯威夫特描绘了小人国的政治。该国有两个党,一个党的成员穿高跟鞋,一个穿矮跟鞋。而国王为了平衡两党,则一只脚穿高跟鞋,一只脚穿矮跟鞋,成了跛脚鸭。小人国选总理的办法是比赛走绳技。参加竞选的大臣们需在钢丝上做许多高难动作,包括翻筋斗而不掉下来,才能胜选。斯威夫特讽刺的尖锐很像鲁迅,他这是对两党制和党派争斗整体上的荒诞和无意义做出的最犀利的嘲讽。小人国还因为敲鸡蛋应该敲大头还是敲小头与持不同意见的邻国战事不断,并要求格列佛去灭掉该国。这就是斯威夫特对英法两国的宗教争端的嘲笑,说明他能够超越宗教和党派之争看到英国社会和宗教矛盾的实质。另外,在《格列佛游记》里,斯威夫特还讽刺了英国的时政。在第三卷“飞岛”中,他把英国比作一个飞岛,在陆地上征服了一些岛国,要求他们纳贡和上税,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纳贡,飞岛就会飞临他们上方遮住他们的雨露和阳光,甚至会降落到他们的头上,摧毁地上的房屋和林园。这些描写明显是批评英国的海外殖民。
看透了两党斗争实质的不仅斯威夫特,笛福比他做得更彻底。斯威夫特虽强烈批评两党争斗无意义,但他没能做到不加入一党。而笛福没有固定的党派立场,他同时为两个政党做事,因为他需要赚钱,更因为他精力旺盛,想要施展他的才能。他为一个党写文章的同时,又为另一个党做情报工作,甚至参加了说服苏格兰加入大不列颠王国的沟通活动。为此,他在20世纪之前的文学界曾被指责为两面派。但我更认为笛福是看透了两党争斗乃权力之争,于是十分务实的他选择了不分党派地多做些实事。
2.反映海外扩张和资本积累的作品
18世纪英国开始大规模海外扩张,占有殖民地。在此阶段的文学中反映海外殖民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鲁滨孙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不愿听从父命继承家业,在伦敦过舒适安稳的日子,而是要冒着各种危险不断出海。他贩卖奴隶、积累资本、在海外开发殖民地,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曾以他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典型例子。对于他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出海冒险的冲动,鲁滨孙没有答案,他说自己天生就有“游荡的嗜好”。直到他60多岁,在《鲁滨孙漂流记续集》里,他又再次离家出海去冒险。我们过去简单地把这种冒险冲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攫取财富的贪婪。但是,当他已身缠万贯,十分富有,而且年迈体弱时,他还要出海冒险,这样的行为如果只用贪财来解释就说不过去了。实际上,在鲁滨孙身上展示的是上升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他们在不择手段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有很积极的一种上进和奋斗精神。18世纪因为科学发展,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对博大的世界发生兴趣,比如地理知识一时成为上层沙龙和客厅里的时髦话题,连太太小姐也以能说一两个欧洲之外的地名来炫耀自己。鲁滨孙这个人物就表现出新兴资产阶级对广阔世界的极大好奇心,对验证自己独立人格和能力的强烈要求,并从这种追求中获得精神满足。他这种要劳动、要占有的个人奋斗精神是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产物。当然,在英国奋斗发家的追求还来自清教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而鲁滨孙的故事就是对这一论断的形象揭示,是对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生动展现,有很强的时代性。
3.反映佃农经济瓦解、城乡对立的作品
15~16世纪的圈地运动开始,英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就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农业凋零,丢失了土地的农民大批流落到城镇,没有了生计。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7-1535)在他的著作《乌托邦》(Utopia,1516)里的名言“羊吃人”就是对圈地养羊,发展纺织业之后农民悲惨境遇的最尖锐的批评。到了18世纪,以世界大都会伦敦为代表的大小城市逐渐在英国成形。在乡村里,土地贵族虽然没落,却还能维持庄园生活,并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很多贵族也开始经商与城市资产阶级逐渐融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英国文学中出现了把城乡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美化乡村、哀叹田园式生活消亡,认为城市是黑暗和邪恶化身的作品在18和19世纪不断出现,形成一种思潮。比如18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的长诗《荒村》、华兹华斯的诗歌《迈克尔》、狄更斯的小说《远大的前程》《雾都孤儿》等,都充满了对失去善良、平静的乡村生活的惋惜和对与乡村对立的浮华、势利又充满罪恶和暴力的城市的抨击。18世纪小说家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的《弃儿汤姆·琼斯传》(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1749)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暗藏着一个结构性的城乡对立的寓意。该小说在文体上是包揽了整个英国城乡生活的全景式小说,它在故事层面上讲的是弃儿汤姆曲折的成长过程。他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考验,战胜了同母异父弟弟的阴谋诡计之后,终于认祖归宗,成为远近乡里的模范士绅。然而,作者十分用心地把小说的18卷工整地分成了乡村、旅途上和伦敦各六卷的叙事架构,而这样的架构刚好完美地对应和承载了汤姆的三个发展阶段,因此这部小说被评论界一致称赞为结构最精美的英国小说之一。然而,菲尔丁颇费苦心的6+6+6的小说结构还承载了一个作者要宣传的寓意层面的潜文本,即对乡村淳朴、善良生活的肯定和对城市邪恶的警示。小说的头6卷描述汤姆被善良的乡绅奥尔渥西收养后,在淳朴的乡间成长为一个漂亮、正直、善良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但是缺乏理性,办事冲动而且生活上不够检点。在被弟弟布利非尔不断诬陷后,汤姆被奥尔渥西误会,最后被逐出庄园。于是,就开始了他离开乡村流浪的第二个6卷。起初他想去从军,参加消灭詹姆士党人的战斗,为国效劳,却中途偶遇心上人索菲而掉头追赶她到了伦敦。第三个6卷则描述汤姆在伦敦如何被看上他的贵妇人欺骗,沦为她的面首,道德沦落至最低点。然后,他又莽撞地与人决斗,刺伤对方而被捕入狱。如果对方伤势过重死去,汤姆就有被判死刑的可能。这时,布利非尔的阴谋暴露,在小说的结尾处汤姆与舅舅奥尔渥西相认,回到了庄园,娶了心上人索菲,过上了幸福、恬静的乐园般生活。小说里这个架构明显影射了主人公从伊甸园(虽然有弟弟这样的毒蛇)的天真无邪的生活,到被逐出伊甸园踏上了艰难的自我教育途程,直到进入伦敦这个邪恶的都会,在各种引诱下他沦落到了出卖肉体的地步,最后进入地狱般的监狱。小说结尾时作者不得不用巧合的事态发展来搭救汤姆,他与道德权威奥尔渥西舅舅相认,重返了乡间的伊甸乐园。在这个失去乐园与重回乐园的寓言潜文本中,菲尔丁对乡村的赞美以及对大城市邪恶的鞭挞态度非常明显。如果说,工业化后凋零的乡村的美好更多是他的一种乌托邦理想,那么作为伦敦的一名司法官,他对当时充斥着犯罪的大城市的邪恶的认识并非空穴来风。因此,他这部小说帮助我们认识了18世纪城市初期的诸多问题,以及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可算是也加入了直到19世纪仍有表现的褒扬乡村,贬低城市的潮流。
4.反映姑娘婚恋与成长问题的小说
从18世纪,特别是中后期,一直到简·奥斯丁的创作,年轻姑娘的婚恋问题就成为文学的一大关注点。其原因主要来自英国工业革命和乡村衰落之后,大批妇女被剥夺了手工劳动的生计,进城务工的农村女人们大多做了仆女,而中等家庭和乡村小地主的女儿们也面临多舛的命运。因此,女孩子能否嫁入有钱人家就成为父母们最操心的事情,成为一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主题。而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村女孩子沦落为妓女和小偷则成为了当时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理查逊就致力用书信体小说谆谆引导女人们要警惕,要洁身自爱,否则一失足就铸成千古恨。范尼·伯尼和海伍德夫人等女作家的小说也围绕这同一个议题做文章,但更偏重写年轻姑娘的成长。到世纪末,奥斯丁的不少小说仍在关注这个议题,特别是在《傲慢与偏见》里她温和地讽刺了急于为五个女儿寻找富有婆家的班奈特夫人。可以说在整个英国的文学史上,只有18世纪下半叶这么集中地出现了姑娘婚恋小说,这乃是当时社会状况所致。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被尊为后来英国心理小说的鼻祖,[4]他的两部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又名美德有报》(Pamela,or Virtue Rewarded,1740)和《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小姐的历史》(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1741-1748)分别写了一个农村姑娘帕美勒在贵族B先生家做仆女的遭遇,以及富商之女克拉丽莎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被恶少钻了空子,而遭奸污的悲剧故事。理查逊是印刷徒工出身,从年少时就常给周边的女人代笔写信和读信。这个经历使他十分了解女性和女性的问题,也逐渐练成了一个写书信的高手。当时伦敦小偷和妓女比比皆是,他们命运悲惨,偷些许食物或布匹就会被关进新门监狱,结果不是上绞架,就是被终身发配到新大陆的弗吉尼亚。中年的理查逊成为有影响的印刷商之后,就逐步出版尺牍和行为指南来教育大众,最后发表了上述两部作品,成为与菲尔丁并列的重要18世纪小说家。帕美勒的故事教导年轻女孩子要抵制各种诱惑,保持贞洁,只有这样才会因美德而获好报。具体来说,帕美勒坚决抵制少东家的骚扰,挑逗和囚禁,坚决不做他的情妇。最后她的美德感化了B先生,把她明媒正娶为夫人。这部小说虽然存在用书信形式长篇自叙惊险遭遇而很不自然的毛病,虽然保持贞洁就会有好报像是用贞洁待价而沽,但在发表的当时却成为十分轰动的畅销书,因为理查逊小说的问题针对性很强。小说《帕美勒》针对了当时有钱人玩弄仆女后抛弃她们,令她们沦为小偷或妓女的严重社会现象。他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富家女孩子往往不喜欢老实无趣的男人,梦想自己有能力把浪荡公子改造好再嫁给他。不同于贫穷出身的帕美勒,克拉丽莎美丽、有教养和文化,还有属于自己的钱财,但是犯了自信的错误,寄希望于改造浪荡贵族拉夫莱斯,而最后惨遭强暴。这部小说是英国第一部悲剧小说,震动了整个欧洲,歌德和卢梭都受其影响。理查逊用书信体裁进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充分反映了当时姑娘们面临婚恋困境时的各种压力和痛苦。
弗朗西丝·伯尼(Frances Burney,又名范尼·伯尼,1752-1840)是18世纪后半期众多女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也是奥斯丁之前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她著有多部女性小说,其中书信体的《伊夫莱娜,或少女涉世录》(Evelin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s Entrance into the World,1778)最为成功。伯尼有好几本小说都写“少女涉世”的话题,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女孩子进入社会的种种困难,甚至是危险处境。伊夫莱娜的母亲产下女儿就死去,临死将她托付给牧师威拉斯抚养。她出落成美丽的姑娘,并接受了牧师良好的教育。但她在远离喧嚣的安静乡村长大,没有任何社交经验。故事主要描述她随友人来到伦敦,因为没有父亲,家事不明,在社交场合饱受轻视和奚落,还不断遭到花花公子们骚扰,直到她遇到正直的年轻绅士奥威尔伯爵,多次得到他出手救助,情况才有了好转。经过许多误会和曲折,在小说结尾处两人喜结良缘,伊夫莱娜也得到了父亲的接纳。伊夫莱娜的遭遇具有时代代表性。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身份被看得很重,身份缺失的女人被边缘化,处境尴尬又不安全。伊夫莱娜不仅要像帕美勒那样拼命捍卫自己的贞操,还要竭力维护自己的淑女形象。伯尼一生关注女人的生存状况,也很真实地用她的小说反映了18世纪家庭和婚恋的各种问题。
结语:18世纪英国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上述对18世纪部分作者和小说的评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欣欣向荣又充满矛盾和问题的英国,看到了一个以大都会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并积极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英国。那个英国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相隔三四百年,但实际上并不遥远。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英国有质的区别,但处在发展市场经济阶段上的中国,还是可以从18世纪英国找到不少可比之处。比如我国目前的图书市场和文学、文化、影视的大众化,比之前任何时期都更接地气;又比如我们也正在建设漂亮的城市,农业人口正大量流入城市,农村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但是,表面上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却不能掩盖时代和制度不同带来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拿农村的变化为例,党中央在发展大都市的同时,同样重视了农村建设及生态环境发展,可以说是以迅疾的速度,一举三得地完成着英国花了近乎一两个世纪才慢慢完成的浩瀚任务。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也没有出现农村破产和萧条。相反,新农村在青山绿水中建成,脱贫成为重中之重的国家工程。所以,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并没造成18世纪英国那种乡村消亡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多世纪文人们的哀伤。大批人口流入城市难免出现一些治安问题,但我们也绝对不存在18世纪伦敦的混乱和肮脏,北京等大城市也没有伦敦当年那种地下贼窝或满街的妓女。再拿英国上升资产阶级的海外扩张为例,目前发展了市场经济的中国也需要海外市场。虽然鲁滨孙进行了殖民活动,但新兴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来积累财富的精神,也没有被马克思否定,特别是我们目前也在提倡“奋斗就是幸福”的世界观。然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海外贸易与鲁滨孙的冒险和奋斗目标绝不相同,我们旨在为全人类的福利奋斗。中国走向世界遵循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通过平等贸易的伙伴关系共同受益。
但是对比18世纪英国,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却不如他们,那就是我们的文人作家没有18世纪英国的这些小说家对社会道德的责任感和担当。上述评介的小说家们面对市场经济和追求物质利益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个个以正能量来教育大众。相比之下,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精英不管目前国家发展阶段的需求,就不加批评和鉴别地追随后现代腐朽、颓废和消极的文学潮流,吹捧那些离中国现时社会尚远的后现代西方文学和影视作品,不管它们是否在宣扬自杀、同性恋纠结,还是暴力和色情。这种作家文人道德责任的缺失就是我们参照18世纪文学时要自叹不如的重要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研读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1] 汉诺威的乔治是16世纪英国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代。
[2] 基于现代英国小说的兴起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有的评论家把现代小说看成中产阶级的文类。可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也有评论家称小说为女人的文类,可参见Ruth Perry,Women,Letters,and the Novel(New York:AMS Press,Inc.,1980)。
[3] 上述这一段里对18世纪英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简介来自Paul Langford著《18世纪英国:宪制建构与产业革命》,刘意青、康勤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二章“罗宾政府的兴起”,第133~170页。
[4] 伊恩·沃特把理查逊和菲尔丁定位为分别引领心理小说和全景社会小说的英国小说之源头。可见Ian Watt著The Rise of the Novel(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