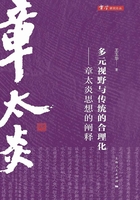
二、激进与保守的震荡
“呜呼!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 在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之下,近代中国的文化分子,开始陷入内心的巨大恐惧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为了重建一个新的富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秩序,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中国出现了两大相互攻难的社会文化思潮,即:欧化主义思潮与传统主义思潮。到了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对中国迫压的加剧,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即民族主义思潮。这些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交互激荡,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斑斓多彩的画面。
在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之下,近代中国的文化分子,开始陷入内心的巨大恐惧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为了重建一个新的富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秩序,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中国出现了两大相互攻难的社会文化思潮,即:欧化主义思潮与传统主义思潮。到了二十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对中国迫压的加剧,又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即民族主义思潮。这些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潮,交互激荡,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斑斓多彩的画面。
1. 由渐而巨的欧化主义思潮
欧化主义思潮的涌动者,是近代中国的欧化派。近代中国的欧化派,由于时代及知识背景的差异,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主张不尽相同。然而,对于处在不同时段的欧化派来说,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基本思维模式却是大体一致的,即无论处于哪一个时段的欧化派,都是将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方向界定在向西方学习的坐标之上。在近代中国,随着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欧化派经历了由“器”而“政”而“教”的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与之相随,欧化派也由“器”而“政”而“教”,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浪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曾经将一个整合的文化系统分成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他认为:
技术系统是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诸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组成的,借助于该系统,使作为一个动物种系的人与自然环境联结起来,我们在这里发现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攻防手段等。社会系统则是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在这个范畴中,我们发现有社会、亲缘、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娱乐等系统。思想意识系统则由音节清晰的语言及其它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神学、传统、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组成了这个范畴。
近代中国的文化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基本上也是经历了一个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思想意识系统的渐次深化的过程,他们将其化约为“器”“政”“教”。由于近代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化过程,所以由他们掀起的欧化主义思潮,也经历了一个由渐而巨、由偏而全的过程。大致说来,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将向西方学习局限在“技术系统”(器)层面,早期维新派则涉及“社会系统”(政)层面,而维新派则突破了前二者,涉及“思想意识系统”(教)层面。
最初的欧化主义思潮,是由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掀起的,他们仅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技术系统”部分的优长,不承认西方文化中“社会系统”与“思想意识系统”部分的优于中国,试图在“中体”的框架内将西方的“技术系统”(“西用”)移植进中国文化的统系之中,以“中体西用”作为文化整合的理论框架,将欧化的程度定位在“西用”上。如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曾经说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
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 。邵作舟也主张“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
。邵作舟也主张“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 。承认中国文化的“技术系统”不如西方,并且主张采取“西用”,这意味着要将这一系统进行西方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注意于船械,兴想于制造,而推本于格致,于是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
。承认中国文化的“技术系统”不如西方,并且主张采取“西用”,这意味着要将这一系统进行西方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注意于船械,兴想于制造,而推本于格致,于是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 。洋务运动期间,由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所开出的这一新的中国文化的演化方向,为西学的大量延入提供了方便之利。然而,因其重点被局限在军事领域内,则影响了中国文化重建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梁启超曾经指出:
。洋务运动期间,由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所开出的这一新的中国文化的演化方向,为西学的大量延入提供了方便之利。然而,因其重点被局限在军事领域内,则影响了中国文化重建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梁启超曾经指出:
(洋务)不外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
洋务派当时之所以要将向西方学习、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运动,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当时文化分子识见的偏狭,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出于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当时一个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栏作家干德利,对此曾经发表过一段肯綮之论,其云:
也许因为中国是被强迫开放与外国通商的缘故,所以它最初表示愿意采用的西洋方法自然是在武器方面。它认为它的战败是由于外国武器和舰艇的优越性,所以它自然地愿意在这方面和这些近代的敌人并驾齐驱。因为它对西洋的武器的价值作这样的估价,所以便建设造船厂和兵工厂。
汤因比则认为:
当十九世纪之际,远东的政治家们似乎认为采取显著优越的技术是一合理的冒险与迫切的需要,此足以表示为他们从西方选择一些他们并不感到有何兴趣的事物,因为,这比之被西方人征服及臣服,无论如何是一“较少的罪恶”。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这一时期由洋务派主导进行的文化运动,也染上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且带有着浓厚的情绪化倾向。盖当时的文化分子害怕失去自己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中“社会系统”及“思想意识系统”层面的价值,便拼命地加以护持,理智的宝刀在此失去了它的锋芒。正是由于这样,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在主张进行“技术系统”欧化的同时,卫道心理则显得甚为迫切。如薛福成认为:
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民生之用,中外所同也。……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得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
王韬则更加语气坚定地认为:“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 对“道”的护持愈烈,说明其内心所遭受的文化挫折感愈强,这种隔裂“体”“用”或者“道”“器”的做法,虽然暂时地可以抚慰这部分受到创伤的文化分子的心灵,但它毕竟无济于事,因为西方的“器”根连于它的“道”,其“用”乃其“体”之“用”。文化本为一整合的系统,割取一部进行异体移植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兴建了许多新式近代企业及近代海陆军,但是,由于制度规设与管理理念仍然是传统的,所以,它导致了橘淮为枳的局面,洋务运动也因此以失败而告结束。随着洋务运动弊病之愈益呈露,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在其所作的“否定”的批评之中,实现了对于这一思潮的扬弃与转进。郭嵩焘云:
对“道”的护持愈烈,说明其内心所遭受的文化挫折感愈强,这种隔裂“体”“用”或者“道”“器”的做法,虽然暂时地可以抚慰这部分受到创伤的文化分子的心灵,但它毕竟无济于事,因为西方的“器”根连于它的“道”,其“用”乃其“体”之“用”。文化本为一整合的系统,割取一部进行异体移植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兴建了许多新式近代企业及近代海陆军,但是,由于制度规设与管理理念仍然是传统的,所以,它导致了橘淮为枳的局面,洋务运动也因此以失败而告结束。随着洋务运动弊病之愈益呈露,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在其所作的“否定”的批评之中,实现了对于这一思潮的扬弃与转进。郭嵩焘云: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又云: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郭嵩焘在此认识到了西方文化中“体”“用”的血脉相连关系,并且大胆地承认了西方的“政教风俗”胜于中国。这种认识的出现,为欧化主义思潮之突破“技术系统”层面,提供了思想基础。不特郭嵩焘,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洋务派大员像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如张树声即曾经这样说道: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伴随着对于西方“政体”价值的认识,遂使这一由洋务派率先推进的欧化主义思潮,在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新整合时,终于突破了“技术系统”层面,而转进至“社会系统”层面。欧化主义思潮之转入“社会系统”层面,既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又是对前一阶段的承续与升华。一部分从洋务派脱胎而来的文化分子,形成了早期维新派,他们在继洋务派之后成了执思想文化界牛耳的时代骄子。这些人大多游历过西洋,西学知识较之洋务派来说要广博得多,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较之洋务派来说也要深刻得多。因此,由他们掀起的文化思潮,其欧化程度便也较前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其所注目的焦点,则由前一时期之注重“军事”与“商务”而进至西方之“政”上,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宪政体,并将此置为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中心。王韬曾经考察过西方国家的政体,他认为:
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意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他又说道:
《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之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他将英国式的君宪政体当作最完美的政体来看待,在“三代遗意”的幌子下,公然鼓吹之而不遗余力。类似的看法在早期维新派中相当普遍,如郑观应云:
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坚船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他同王韬一样,也将“议院”当作治国之本、富强之基。他又说道: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
他也将英国式的君宪政体当作最完美的政体来看待,并要求在中国“亟行”此制 ,认为:“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
,认为:“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 如果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背公法哉!”
如果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背公法哉!”
以上王韬、郑观应二人的看法,基本上也反映了当时早期维新派群体的变政主张,所以,其他人的言论我们在此无需再繁征引。早期维新派所称道的西方君宪政体,相当于洋务派所说的“体”,主张在中国“亟行此制”,则意味着要在中国进行“体”的欧化,洋务派固守的藩篱,在此被突破了。但就早期维新派本身而言,他们当时并没有觉得“亟行”欧西的君宪政体,是同传统中国的政制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当时,中国传统的政制并没有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毋宁是将其变政主张当作中国传统政制的补充来看待的,他们认为欧西诸国所行的君宪政制符合“三代遗意”,在中国之“亟行”西方的君宪政体,不过是对于传统中国政制的刮垢磨光。然而,早期维新派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进行重建的努力,至这一层次便停止了,至于支撑传统政制的纲常伦纪,则仍然受到他们的严格保护。但堤防一旦决口,便会势不可挡,在早期维新派的后辈那里,“体”的欧化,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政制的对立面出现,而且其矛头所向,也直接指向了传统的专制政制,并且,支撑这一传统专制政制的纲常伦纪,也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批判。欧化主义思潮在此终于地冲向了它的顶点,它化成了一场否定传统、再造新邦的“维新运动”。
如果说早期维新派将欧化的程度仅仅局限在“社会系统”层面的话,那么,在其后辈维新派那里,则越进至“思想意识系统”层面了。在维新派那里,西方文化的价值,开始得到了全盘的肯定,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诸价值,则成了他们诠释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中国的文化分子被进一步地激怒了,传统文化被他们看成为导致中国衰败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将西方文化确立为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参照系,对传统文化作一次全面而彻底的革新。这一阶段的欧化主义思潮,对传统文化作了一次彻底清算。其中攻击传统文化最厉害的要数谭嗣同与樊锥了,此二人皆是湖南的激进的年轻改革思想家。谭嗣同对于二千年来的“政”,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否定传统之“政”的同时,谭嗣同还形成了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产生的社会契约思想。他认为:
。在否定传统之“政”的同时,谭嗣同还形成了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产生的社会契约思想。他认为: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较之早期维新派在“三代遗意”的幌子下模效西方君宪政体的做法,在理论上要更具深度,且也更具有说服力。在否定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制时,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锋芒指向了支撑这一传统专制政制的纲常伦纪。他认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此,方愈剧矣。” 并云:“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
并云:“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 更为大胆的是,谭嗣同对于二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的“学”,也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它是“工媚大盗”(即传统的专制政制)的伪学。
更为大胆的是,谭嗣同对于二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的“学”,也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它是“工媚大盗”(即传统的专制政制)的伪学。 与此相反,他对于西方文化则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并对洋务派之将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在“技术系统”层面,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谭嗣同云:
与此相反,他对于西方文化则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并对洋务派之将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在“技术系统”层面,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谭嗣同云:
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况枝叶尚无有能讲者。
他以洋务派的“枝叶之变”为不可取,他自己寻求的则是“根本之变”。为此,他对由洋务派所揭出的“道器观”,也重新作了界定,认为:
特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倘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谭嗣同以“器”为“体”,以“道”为“用”,认为“道”即寓之于“器”之中,显然与洋务派揭橥的“道体器用”或者“道本器末”的“道器观”是相对立的。谭嗣同的这一“器体道用”“器道俱变”的思想,虽然继承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气学”思想流脉,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因为,根据他的这一“器体道用”“器道俱变”思想,在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时,不可避免地,在采行“西用”时,便意味着同时也要采行“西体”,在变“中器”时,便意味着同时也要变“中道”,在此,全盘西化实际上是呼之欲出了。谭嗣同在当时高呼要“冲决网罗”,使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主张充满了浓厚的激进主义的色彩。然而,在其彻底否定传统的呐喊声中,他却仍然为传统留下了最后一块招牌,即“尊孔”的空名,这大概是受到康有为今文思想的影响所致。尽管如此,谭嗣同所谓的孔子,也已经不是传统的孔子的形象了。当时,谭嗣同所尊奉的孔子,乃是经他之手重新塑造之后的欧化形象的孔子了。如他曾经这样说道:“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因为,根据他的这一“器体道用”“器道俱变”思想,在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时,不可避免地,在采行“西用”时,便意味着同时也要采行“西体”,在变“中器”时,便意味着同时也要变“中道”,在此,全盘西化实际上是呼之欲出了。谭嗣同在当时高呼要“冲决网罗”,使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主张充满了浓厚的激进主义的色彩。然而,在其彻底否定传统的呐喊声中,他却仍然为传统留下了最后一块招牌,即“尊孔”的空名,这大概是受到康有为今文思想的影响所致。尽管如此,谭嗣同所谓的孔子,也已经不是传统的孔子的形象了。当时,谭嗣同所尊奉的孔子,乃是经他之手重新塑造之后的欧化形象的孔子了。如他曾经这样说道:“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 孔子在他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位废除君主专制,倡行民主政体的变法大师。谭嗣同的这一矫情之论,我们实也可视之为维新派的一种自我影像的折射。
孔子在他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位废除君主专制,倡行民主政体的变法大师。谭嗣同的这一矫情之论,我们实也可视之为维新派的一种自我影像的折射。
如果说谭嗣同是在“尊孔”的名义下主张全盘欧化的话,那么,樊锥则连这块孔家店的招牌也揭下了,他主张对于传统要全盘扫荡,义无反顾地进行全盘欧化。他曾经对于生活在“意想世界”里的自大的孔子之徒,给予了辛辣的嘲讽,认为“世之自命孔子之徒,昂昂儒服,以为舍我之外必无天地,舍我之外必无教化,是非能真见其无者,意想其心如此而已。” 在尽情地嘲笑传统儒生们盲目自大、无知意想的时候,樊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概扫荡的态度,将中国文化新命的再造,寄托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模效上。下面所列的两段文字,可谓是樊锥激进反传统思想和全盘欧化主张的典型话语表述,其云:
在尽情地嘲笑传统儒生们盲目自大、无知意想的时候,樊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一概扫荡的态度,将中国文化新命的再造,寄托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模效上。下面所列的两段文字,可谓是樊锥激进反传统思想和全盘欧化主张的典型话语表述,其云:
是故,非刳剔腐肉,吸灭败气,扫除一切,伐毛洗髓,则不足活其性,畅其新血,振其以太,清其脑筋矣;是故,非毅然破私天下之猥见,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权之义,出万死以图一生,则不足斡转星球,反旆日月,更革耳目,耸动万国矣。
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
将文化的重建定位在“扫除一切”、“唯泰西者是效”上,其欧化的激进程度,至此盖已无可复加。这种全盘反传统及全盘欧化的文化主张,同其五四时期的后辈们相较,丝毫也不显得逊色。这一激进主义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主张,犹如火山喷发,极大地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然而,这一激荡于戊戌时期的激进主义的欧化思潮,盖丁时未至,未能像五四时期那样影响广远,但它对于晚清时期一批又一批的趋新知识分子之脱离传统羁绊、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则有着扫除廓清之功。并且,它还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运动,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资源,其功不可掩。
2. 守成拒新的传统主义思潮
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传统主义,指的是一种在每一个人那里都多少存在的形式的心理属性。” 并且认为:“我们常常固守旧方式,不愿意接受新文明,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倾向。”
并且认为:“我们常常固守旧方式,不愿意接受新文明,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倾向。” 人们通常又将这种人类普遍所具有的“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也即“传统主义”,称之为“自然保守主义”,
人们通常又将这种人类普遍所具有的“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也即“传统主义”,称之为“自然保守主义”, 以区别于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现代现象”出现的“保守主义”,也即“现代保守主义”。
以区别于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现代现象”出现的“保守主义”,也即“现代保守主义”。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昔日的辉煌,同人类天生所具有的“保守心理倾向”相结合,为近代中国传统主义的滋生与流衍,提供了极为深厚的土壤。殷海光教授曾经指出:“就社会文化的意义来说,孔制门徒一生下来就是保守主义者。所以保守主义在中国文化里不仅势力雄厚而且根深蒂固。”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即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昔日的辉煌,同人类天生所具有的“保守心理倾向”相结合,为近代中国传统主义的滋生与流衍,提供了极为深厚的土壤。殷海光教授曾经指出:“就社会文化的意义来说,孔制门徒一生下来就是保守主义者。所以保守主义在中国文化里不仅势力雄厚而且根深蒂固。” 伴随着欧化主义思潮之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趋于激进化,自然地也会激起“传统主义”的反抗。一部分固守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的文化精英,对于当时兴起的欧化主义思潮,奋力地进行抗争,掀起了传统主义思潮。他们反对将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界定在欧化取向上,企图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随着欧化思潮之由器→政→教的推衍,由这些固守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的文化分子掀起的传统主义思潮,便也经历了同样的反动与对抗的过程。然而,通过仔细寻绎传统主义思潮之内在理路,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反对欧化、护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传统主义思潮,却主要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在其思维程式里,我们很难找到理性运作的痕迹。卡尔·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
伴随着欧化主义思潮之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趋于激进化,自然地也会激起“传统主义”的反抗。一部分固守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的文化精英,对于当时兴起的欧化主义思潮,奋力地进行抗争,掀起了传统主义思潮。他们反对将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界定在欧化取向上,企图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随着欧化思潮之由器→政→教的推衍,由这些固守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的文化分子掀起的传统主义思潮,便也经历了同样的反动与对抗的过程。然而,通过仔细寻绎传统主义思潮之内在理路,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反对欧化、护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传统主义思潮,却主要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在其思维程式里,我们很难找到理性运作的痕迹。卡尔·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 当时中国的传统主义者,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传统主义者一样,在欧风东渐的时代大潮面前,也只能完全地处于一种被动反应的地位。尽管他们在反击欧化主义者的思想意旨时,表现得也是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他们却拿不出更好的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方案,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传统主义者的普遍的“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罢了。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陷入危机之后,具有浓厚“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的传统主义者,选择“守成拒新”的文化思维模式,是难以胜任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秩序重建这一历史大任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传统主义者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与新的历史挑战面前,其内在的自我调适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
当时中国的传统主义者,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传统主义者一样,在欧风东渐的时代大潮面前,也只能完全地处于一种被动反应的地位。尽管他们在反击欧化主义者的思想意旨时,表现得也是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他们却拿不出更好的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方案,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传统主义者的普遍的“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罢了。这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陷入危机之后,具有浓厚“对旧方式的依恋”的“保守心理倾向”的传统主义者,选择“守成拒新”的文化思维模式,是难以胜任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秩序重建这一历史大任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传统主义者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与新的历史挑战面前,其内在的自我调适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
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皇权轻民权,重纲常名分,严夷夏大防等等,乃是中国传统价值谱系在社会层面展开之后呈现出的主要面相。由此,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每当社会发生衰乱与危机时刻,其解救的措施,往往便是诉之于道德的重振。敦风俗、振纲纪,由之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衰乱与危机时刻最为常见的政治话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则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士人的崇高理想。这也使得中国的传统主义者,在实质上都成为“应帝王”式的人物。 纵观在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即使是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其计也往往不过如此。如顾炎武曾经说道:“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纵观在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即使是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其计也往往不过如此。如顾炎武曾经说道:“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又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又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沈子敦曾作有《风俗篇》,对此旨阐发尤详。其云:
沈子敦曾作有《风俗篇》,对此旨阐发尤详。其云:
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恭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
纵观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一部分保守的文化分子掀起的对抗欧化的传统主义思潮,其手中所执的利器,不过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仍然是将当时中国社会之陷入危机,归咎于风俗的败坏与礼义廉耻的失坠。对于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他们也仍然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诉之于道德的重整与风俗的敦厚。如曾经出使过西洋的刘锡鸿,在批评洋务运动时即说道:“中国空虚不在无船无炮,而在无人无材,此皆政教之过也。政教既失,岂唯外洋之足患哉!夫士习之坏,向第阴备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仁义之名;民风之患,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则长幼无序,且并不知有贵贱之分,此等气象,尚能久安无事乎?” 他将中国之所以衰弱的原因,归咎于士习、民风的败坏。在刘锡鸿看来,只要能够整饬纪纲、敦化风俗,则中国自可以自立自强。其云:
他将中国之所以衰弱的原因,归咎于士习、民风的败坏。在刘锡鸿看来,只要能够整饬纪纲、敦化风俗,则中国自可以自立自强。其云:
自强者,自立也,非谓外洋日以兵为事,自示强悍也。赏罚严明,用人得当,以立天下之纲纪,则人才自奋,吏治自修,民生日遂,财赋自裕,兵力自强,外夷亦自慑服,何事纷纷他求?
理学重臣兼有帝师身份的大学士倭仁,也持有着与刘锡鸿同样的看法,且说得更为简截明白,其云: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由此,倭仁同刘锡鸿一样,也是将礼义廉耻当作治国的第一要义来看待,主张“以仁义救天下” 。倭仁在其所作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讲义”中,进一步地推阐孟子的义利观,曾经这样说道:
。倭仁在其所作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讲义”中,进一步地推阐孟子的义利观,曾经这样说道:
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三代之世,所以人心正、风俗醇,治隆于上而教行于下者,以仁义故也;后世吏治坏,民心漓,廉耻道丧而寇贼日兴者,以利故也。千古治乱之机,莫不由此。……治国者何去何从,尚其深思而明辨之哉!
从这一思想意旨出发,倭仁也和传统的儒者一样,重“义利之辨”。他主张“辨义利要如太阿断物,立地分作两畔,丝毫不容相混” 。并且指出:“人心痼蔽,理欲混淆,尚有何事可为?故兴学育材,明义利之辨,是为治第一义也。”
。并且指出:“人心痼蔽,理欲混淆,尚有何事可为?故兴学育材,明义利之辨,是为治第一义也。” 由于倭仁将“明义利之辨”看成是“为治”的“第一义”,他将“利心”、“人之有欲”看成是世间的“耽心物”,是实现“王道”坦途上的最大障碍,因此,他最为关注的便是“明理正心”,他号召人们要打过“声色货利关”,要求人们“三复斯言,猛割一爱”。
由于倭仁将“明义利之辨”看成是“为治”的“第一义”,他将“利心”、“人之有欲”看成是世间的“耽心物”,是实现“王道”坦途上的最大障碍,因此,他最为关注的便是“明理正心”,他号召人们要打过“声色货利关”,要求人们“三复斯言,猛割一爱”。 他曾经指出:
他曾经指出:
心有欲则狭,无欲则宽;有欲则忙,无欲则闲;有欲则险,无欲则平;有欲则忧,无欲则乐;有欲则馁,无欲则刚。须将心头打叠干净,如楼阁在空中然后可。
他认为,天下万事,“无事不坏在一个私字” ,因此,他也和正统的儒者一样,主张通过“内省”的途径,通过个体的“养心”工夫,去克治人们的“私欲”。个体通过内省,“将心头打叠干净”,从而“天理流行”,“天地万物为一体”,形成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文化秩序。在内省克欲的工夫上,他甚至还云:“求仁得仁,饿死何妨?”
,因此,他也和正统的儒者一样,主张通过“内省”的途径,通过个体的“养心”工夫,去克治人们的“私欲”。个体通过内省,“将心头打叠干净”,从而“天理流行”,“天地万物为一体”,形成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文化秩序。在内省克欲的工夫上,他甚至还云:“求仁得仁,饿死何妨?” 由此也可见得倭仁对于个体“养心”工夫要求之严了。由上亦可以看出,倭仁不过是重新复述了充满浓厚内省精神的正统儒学的治世要义。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出发,以倭仁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对以崇尚智、利、力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便深恶痛绝,欧化主义者所推动的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思路,由此便自然地会遭到他们的断然反对。刘锡鸿声称:“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
由此也可见得倭仁对于个体“养心”工夫要求之严了。由上亦可以看出,倭仁不过是重新复述了充满浓厚内省精神的正统儒学的治世要义。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出发,以倭仁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对以崇尚智、利、力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便深恶痛绝,欧化主义者所推动的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思路,由此便自然地会遭到他们的断然反对。刘锡鸿声称:“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 倭仁则认为“变而从夷”,就会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的局面。
倭仁则认为“变而从夷”,就会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的局面。
这一抵制欧化的传统主义思潮,至戊戌时期随着欧化思潮的趋于激进化,其抵抗的程度也愈来愈趋于激烈。如果说,在戊戌以前,以倭仁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之反对洋务派推进的欧化事业,其表现主要呈现的是各自保守思想的自我陈述的话,那么,至戊戌时期,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传统主义者,则互相之间沟通声气,不仅通过著文、书信、弹章等方式表达其固守传统价值的强烈意愿,而且还行动起来,在政治上对主张欧化的维新派成员施以人身攻击与迫害。并且,这些保守的文化分子还将其抵制欧化、护持传统文化价值的言论集结成两本小册子(一曰《翼教丛编》,苏舆编;一曰《觉迷要录》,叶德辉辑),广为散发,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上节所述,戊戌时期,维新派之主张向西方学习,带有着浓厚的激进反传统的全盘欧化的味道,此旨在谭嗣同、樊锥的思想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民权”“平等”等这些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则是当时维新派向国人宣说得最为恳切的思想意旨,并且,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还将其当下的政治奋斗目标,确立为力图在现实中国建立一个有类于西方诸国的君宪政制,主张“兴民权”“设议院”。然而,维新派所主张的“民权”“平等”等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却与中国传统的若皇权至上、纲常名分等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传统主义者,在翼教激情的鼓荡之下,对维新派的思想宗旨施以猛烈的反击,且以捍卫传统的纲常名教为己任。对于当时维新派阐述其维新思想且影响甚大的重要著作若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幼学通议》以及徐仁铸的《 轩今语》等,叶德辉皆曾撰文对之进行驳议。而对于维新派所宣说的“民权”“平等”思想,叶德辉则驳之尤切。他曾经说道:
轩今语》等,叶德辉皆曾撰文对之进行驳议。而对于维新派所宣说的“民权”“平等”思想,叶德辉则驳之尤切。他曾经说道:
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而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水火之中哉!注1
注1:苏舆:《翼教丛编》卷四《叶吏部‹《 轩今语》评›》,第80页。
轩今语》评›》,第80页。
又云:
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虽其间暴主迭兴,中原多故,而圣清之制,则固远轶汉唐,比隆三代也。
叶德辉在其竭力美化传统君主政体的眷眷之情中,对于维新派提倡的“兴民权”宗旨自然要进行反对。叶德辉认为“民有权,上无权矣” ,且云:“民无论智愚,人人得伸其权,可以犯上作乱。”
,且云:“民无论智愚,人人得伸其权,可以犯上作乱。” 因此,在叶德辉看来,“兴民权,只速乱耳”,只会导致中国的灭亡。
因此,在叶德辉看来,“兴民权,只速乱耳”,只会导致中国的灭亡。 对于维新派的“平等”主张,叶德辉则将其视之为坏乱“圣人之纲常”
对于维新派的“平等”主张,叶德辉则将其视之为坏乱“圣人之纲常” ,并且恶毒地咒骂道:“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并且恶毒地咒骂道:“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由此,当维新派大张旗鼓地宣传向西方学习,积极地推进维新运动之时,这些传统主义者便公然地揭起“护圣教”的旗帜。
由此,当维新派大张旗鼓地宣传向西方学习,积极地推进维新运动之时,这些传统主义者便公然地揭起“护圣教”的旗帜。 他们一则认为:“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三代虽有损益,百世不可变更。”
他们一则认为:“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三代虽有损益,百世不可变更。” 一则又认为:“孔教之大,与天地参,其教不待传而自传。”
一则又认为:“孔教之大,与天地参,其教不待传而自传。” 并且还公然地宣言道:
并且还公然地宣言道:
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而其精意所构,则有以辉光而日新。
叶德辉甚至于斥责“谓西教胜孔教者”为“谬种” ,而将维新派所宣说的维新思想称为“异端”
,而将维新派所宣说的维新思想称为“异端” 。他曾经自豪地说道:
。他曾经自豪地说道:
合五洲之大势而论,人数至众者莫如中国,良以地居北极温带之内,气候中和,得天独厚,而又开辟在万国之前,是以文明甲于天下也。
所以,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传统主义者,也仍然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继续牢牢地持守着“华夷之辨”这一古老的藩篱。他们认为:
孔子《春秋》之旨,曰“内中国而外夷狄”,日学《春秋》,云何不知?如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未闻中国而进于夷则夷之也。注2
注2:苏舆:《翼教丛编》卷四《叶吏部‹《 轩今语》评›》,第86页。
轩今语》评›》,第86页。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传统主义者之抗拒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欧化主义者的理论利器,仍然不过是传统的“义利之辨”与“华夷之辨”,这与其前辈倭仁、刘锡鸿等的反对欧化的思维程式如出一辙。由之,对于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他们也像倭仁、刘锡鸿等一样,也是诉之于对于“人心”的拯救。对于维新派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们则将之视之为“煽或人心” 或者是“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为学术人心之大害。
或者是“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为学术人心之大害。 叶德辉认为:“世局有变更,天理人心之公无变更。”
叶德辉认为:“世局有变更,天理人心之公无变更。” 宾凤阳则说道:“夫世运之盛,端在人心;人心之纯,由于学术。”
宾凤阳则说道:“夫世运之盛,端在人心;人心之纯,由于学术。” 所以,拯救“人心”的工夫,在他们看来则有赖于“正学”。作为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与“孔子改制”诸说,他们则直斥之为“伪学”,对此,叶德辉曾经“发指眦裂”,怒斥康有为为“士类之文妖”。
所以,拯救“人心”的工夫,在他们看来则有赖于“正学”。作为维新运动指导思想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与“孔子改制”诸说,他们则直斥之为“伪学”,对此,叶德辉曾经“发指眦裂”,怒斥康有为为“士类之文妖”。
从上面叶德辉诸人的反对欧化言论及其护持传统价值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传统主义者主要是出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偏爱的一种情绪性反应。而潜藏于他们心底的“翼教”激情,则成为他们组织与行动起来的凝结剂。除了思想上的交锋之外,这一时期,这些固守传统价值的传统主义者,还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对维新派施以政治迫害。他们恶毒地咒骂主张“唯泰西者是效”的年轻改革思想家樊锥是“汉奸之尤” ,并且切齿地说道:“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
,并且切齿地说道:“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 而且还大打出手,将樊锥从其家乡邵阳逐出。同情并认可康有为今文学说的一代经今文学大师皮锡瑞,在这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的迫害之下,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而且还大打出手,将樊锥从其家乡邵阳逐出。同情并认可康有为今文学说的一代经今文学大师皮锡瑞,在这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的迫害之下,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下面一段是引自《翼教丛编》的“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由此“告白”,我们可以窥出当时保守的文化分子掀起的传统主义思潮之对抗欧化思潮,是多么地激烈,又是多么地苍白无力。该“告白”云:
下面一段是引自《翼教丛编》的“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由此“告白”,我们可以窥出当时保守的文化分子掀起的传统主义思潮之对抗欧化思潮,是多么地激烈,又是多么地苍白无力。该“告白”云:
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处张帖,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置,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
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曾经指出:“保守主义者惯于运用政府的力量来阻止变动,或限制变动的速度,以满足较怯懦的心灵之要求。” 同样,19世纪末,中国保守的文化分子之对待反对派,也是诉之于政治的迫害与武力的蛮横,维新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落下了帷幕。此后,中国保守的文化分子则利用下层民众的排外心理,在义和团运动中鼓惑团民盲目地仇洋杀教,其仇视西方文化的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致使无数义和团民的鲜血染红了传统文化的泥土。但这场最为悲壮的护教运动,最终还是在西洋文明的枪口之下失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抗拒欧化的传统主义思潮,至此便也终于走完了它自己的历程。
同样,19世纪末,中国保守的文化分子之对待反对派,也是诉之于政治的迫害与武力的蛮横,维新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落下了帷幕。此后,中国保守的文化分子则利用下层民众的排外心理,在义和团运动中鼓惑团民盲目地仇洋杀教,其仇视西方文化的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致使无数义和团民的鲜血染红了传统文化的泥土。但这场最为悲壮的护教运动,最终还是在西洋文明的枪口之下失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抗拒欧化的传统主义思潮,至此便也终于走完了它自己的历程。
当然,在以后的历史年代里,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传统主义者粉墨登场,可是,像晚清时期那样的完全“守成拒新”的传统主义思潮,则被历史的浪涛无情地席卷而去了。在“莽莽欧风卷亚雨”的大震荡时代,随着20世纪初滚滚革命洪流之临至,欧化主义思潮借着撞击传统专制王权政治风暴的强大阵势,彻底地压倒了传统主义思潮。在大音起矣的中国,欧风美雨,如怒涛排卷,不可扼抑。如同具有摧毁一切威力的政治风暴那样,欧风美雨在20世纪初的无比威力,使得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面临着毁灭性的冲击。更多的人在面对失序与混乱时,似乎茫茫然无所适从了。时代在呼唤着“新”,但同时也在呼唤着“理性”,于是乎便出现了对于欧化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反思,加之20世纪初的因缘际会,民族主义思潮便油然而起了。
3. 折中调和的民族主义思潮
1891年夏、冬间,在康有为和朱一新之间,围绕着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打了一场颇为激烈的笔墨官司。朱一新在复康有为的“第四书”中写道:
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出,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今以艺之未极其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吾义理以徇之,何异救刖而牵其足,拯溺而入于渊,是亦不可以已乎?……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归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说导之哉?……一二贤知之士,矫枉过正,又以为圣圣相传之《诗》《书》《礼》《乐》果不足以应变也,而姑从事于其新奇可喜者,以为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谓本原者道,其所〔谓〕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为天下后世所断断不可行者乎?
朱一新反对康有为欧化主张的理由,是中国与戎翟义理各殊,戎翟之义理只能行于戎翟,而不可行于中国;西方之获致富强,自有其“道”之大本,然“其所〔谓〕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朱一新是一个反对欧化、捍卫传统文化的最坚定分子,他同其他的保守的文化分子一样,也是将“正人心、厚风俗”当作挽救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是,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朱一新以为各个民族由于“义理”各殊,规定了其化走向的不同,不能强合为一,不能因为中国文化的末流之失,遂完全否定中国文化。这同其他保守的文化分子纯从激情出发反对欧化的思想,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朱一新的这一文化主张,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色,强调了“民族精神”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存立的重要意义。这一思想逻辑的合理展开,应该是将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在“民族精神”的基础之上,这似乎透出了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些微曦光。惜朱一新未见及此,他仅仅以护持传统的“纲常伦纪”为己任,不能折向对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探求,而为中国文化开出一个新的方向。这也深刻地说明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保守的文化分子,已经无力承担起挽救中国文化的大任了,其思想的锋芒已消失在传统的沉沉夜幕里。
二十世纪初勃然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由“国粹派”掀起的,但他们并不是朱一新思想的传人。民族主义思潮之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兴起,与当时国内、国外政治形势的激荡,以及一部分文化分子对于欧化主义思潮的反思,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世界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全世界的殖民地分割完毕,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不仅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且西方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逞日益尖锐之势。在西方由启蒙时代确立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已经日益为“民族主义”的价值所取代,“民族至上”的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而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留学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一批又一批的大清帝国的留学生,开始走出国门,进入西方世界(主要是进入当时正在推进全面欧化运动的日本)。身处于西方世界,他们对这一世界局势的变动感受颇深,震动极大。有人惊恐道:“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 他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乘风破涛以入于亚”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怪物”,将是灭亡中国的最危险敌人。因此,他们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他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乘风破涛以入于亚”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怪物”,将是灭亡中国的最危险敌人。因此,他们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在西方民族主义“怪物”的迫压之下,中国的民族意识由之也开始苏醒了。由此,当时在中国的“趋新知识群”中,出现了一部分对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深为敏感的文化人,他们对于过去由欧化主义者掀起的欧化主义思潮开始进行反思,并对之采取了激烈批评的态度。余一云:
在西方民族主义“怪物”的迫压之下,中国的民族意识由之也开始苏醒了。由此,当时在中国的“趋新知识群”中,出现了一部分对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深为敏感的文化人,他们对于过去由欧化主义者掀起的欧化主义思潮开始进行反思,并对之采取了激烈批评的态度。余一云:
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主派,皆是矣。夫言各有当,其时,吾诚不敢拾后者以傲前者。所可痛者,则以吾数千年神明之胄,业将迫之于山之巅、水之涯,行将尽其类而后已。环宇虽大,竟无容足之区。病将死矣,曾不知病之所在,死之所由。呜呼!今吾不再试一掬泪,以为吾同胞告,则吾恐终为所噬,而永永沉沦,万劫不复也。
余一对于由“制造派”(即洋务派)、“变法派”(即维新派)、“自由民主派”(即革命派)所推进的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欧化主义取向,采取了全盘否定的立场。他认为由欧化主义者(包括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所推进的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努力,在方向上已经误入了歧途,是不知“病将死矣”的中国“病之所在、死之所由”。他认为,只有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才能挽救中国文化于不坠。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渐渐昭苏的民族意识,折射到对于面临着巨大危机的中国进行社会文化秩序的重构上,则唤醒了中国的一部分文化分子对于“民族精神”的高度重视。
其次,国内局势的变动,则成了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契机。1898年夏天,由保守分子发动的宫廷政变,绞杀了由欧化主义者所推进的维新运动。之后,保守分子又利用普通民众的排外心理,掀起了大规模的仇洋杀教运动,招致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在义和团民众的英勇抗击之下,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可耻地破产了,但在这一事件之后,满族统治者却在洋人面前彻底地屈服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成了满族统治者的治国信条。这不仅动摇了其统治中国的政治权威,而且还唤醒了隐藏在汉人心中的种族意识,于是,“排满”成了政治斗争的最为简截的口号。国内、国际政治局势的交互激荡,终于使民族主义理念以磅礴之势席卷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
如果从思想层面去透视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原因,则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之在中国的兴起,还与当时西方世界主流思想的变化,以及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西方在启蒙时代确立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至19世纪后半期已经日益式微,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虽然出版于1859年,但却无救于自由主义的衰落。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在其所著的《自由主义》一书里曾经指出:至十九世纪末叶,自由主义作为一项伟大运动已经大大地衰落了,“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被霍布豪斯形象地比喻为挤夹“自由主义”之“磨石”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开始取代“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思想舞台的主流地位。这一思想主流的变化,也被当时敏锐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所觉察。如当时即有人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被霍布豪斯形象地比喻为挤夹“自由主义”之“磨石”的“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开始取代“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思想舞台的主流地位。这一思想主流的变化,也被当时敏锐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所觉察。如当时即有人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并且指出:“二十世纪之自由与公义之腐败,必将过于十九世纪之末。”
,并且指出:“二十世纪之自由与公义之腐败,必将过于十九世纪之末。” 刚刚受到过西方启蒙思想洗礼不久的中国思想界,很快地便接受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这显示了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急速变化的特点。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受纳,就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刚刚受到过西方启蒙思想洗礼不久的中国思想界,很快地便接受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这显示了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急速变化的特点。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受纳,就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运动的中心是在日本。由于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加之当时日本是亚洲向西方学习唯一成功的国家,所以,它成了中国趋新知识群心目中成功的典范。时人普遍地认为,通过学习日本,即可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吸收进来,且有节时省工之效。随着大批趋新知识分子之涌入日本,随着这些趋新知识分子与日本思想界接触之渐趋密切,不可避免地,日本思想运动的变化,也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了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脱亚入欧”的欧化运动,其历史上著名的“鹿鸣馆时代”(1883—1887),即是出现于此一时期。“鹿鸣馆时代”之出现,反映了日本朝野上下欧化的决心,及其醉心于欧化的程度之深。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之下,日本的欧化浪潮渐趋巅峰。“一八八六到八八年间的冬天,对东京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季节,老百姓被鼓励穿着洋服,同时在其他各方面也尽量地采取西式的仪节。” 然而,随着日本欧化浪潮的日益高涨,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辰巳小二郎等人组织了“政教社”,并于同年4月创刊《日本人》杂志,主张尊重“国粹”,反对欧化。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23年才结束。“政教社”派特别重视对于“民族性”(政教社派使用的“国粹”一词,乃是西文nationality的日译词汇,志贺重昂将其释之为“民族性”)的持护,主张小心地、有选择性地处理外来文物,以免损及民族生存之钥的“国粹”。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马丁·白乃尔(Martin Bernal)曾经指出,在日本出现的“保存国粹”观念,“立刻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向日本借用名词。当中国第一波西化浪潮(1898—1906)过后,日本人的活动也直接启发了他们的灵感”
然而,随着日本欧化浪潮的日益高涨,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辰巳小二郎等人组织了“政教社”,并于同年4月创刊《日本人》杂志,主张尊重“国粹”,反对欧化。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23年才结束。“政教社”派特别重视对于“民族性”(政教社派使用的“国粹”一词,乃是西文nationality的日译词汇,志贺重昂将其释之为“民族性”)的持护,主张小心地、有选择性地处理外来文物,以免损及民族生存之钥的“国粹”。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马丁·白乃尔(Martin Bernal)曾经指出,在日本出现的“保存国粹”观念,“立刻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向日本借用名词。当中国第一波西化浪潮(1898—1906)过后,日本人的活动也直接启发了他们的灵感” 。作为中国“保存国粹”运动的核心人物,刘师培认为:“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
。作为中国“保存国粹”运动的核心人物,刘师培认为:“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 邓实在叙述创立《国粹学报》的缘起时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其云:
邓实在叙述创立《国粹学报》的缘起时也有着类似的看法,其云:
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第一编,以告海内曰: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弛贵族之权,削封建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兴,达泰(今译为但丁——笔者)氏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昔者日本维新,归藩复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雄鸡鸣而天地白,晓钟动而魂梦苏。天下志士,其有哀国学之流亡者乎?庶几披涕以读而为之舞。
由此亦可见出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日本“保存国粹”运动的渊源了。日本的“保存国粹”运动,之所以“直接启发了他们的灵感”,乃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日本的“保存国粹”运动,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有着相同的反思欧化主义的思想担当之故。
在西方,“民族主义”是继“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一大政治思潮,它将“民族”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来考虑,确立了“民族”的主体地位,而“个人”则被置于从属的、客体的地位。“自由主义”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民族主义”则主要是十九世纪西方诸国进行民族建国运动的理论体现,它们在西方的确立,分别花了将近二百年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派提出“扩充民权”的要求,可视为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之始的话,那么至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之传入中国止,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仅仅还只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所以,在“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尚处于初始阶段。况且,当时中国人民正在同专制王权作斗争,“自由主义”所持奉的价值,仍然是他们最为重要的基本理念,这样,“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不会像在西方那样成了过时之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后,便发生了深刻的折变。在西方,“民族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在中国,“民族主义”则成了“自由主义”的有力补充。也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往往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在主张建立民族国家,提倡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同时,仍然奉行“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的价值。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西文nationality含有“民族性”、“民族精神”诸意,当日本的政教社派将其译为“国粹”一词加以使用时,曾经对之作过一般的界定,意指:(1)一种无形的精神;(2)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3)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日本“保存国粹”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均是当时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家,他们担心随着日本欧化浪潮的推进,将会导致日本固有民族精神“大和魂”的失落,主张日本之向西方学习,应以“民族和国家的特色为媒介”,“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之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 。反对像欧化派那样对于西方文化进行生硬照搬,所以,“民族性”或“民族精神”,便成为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重要资源。与日本的政教社派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精神”对于一个民族存立的重要意义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之所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结合,因道德与感情之结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日薄于大陆之上。”
。反对像欧化派那样对于西方文化进行生硬照搬,所以,“民族性”或“民族精神”,便成为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重要资源。与日本的政教社派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精神”对于一个民族存立的重要意义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之所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结合,因道德与感情之结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日薄于大陆之上。” 像“德意志之所以统一,意大利、希腊之所以独立,腓律宾、图兰斯法耳之所以抗击强敌”
像“德意志之所以统一,意大利、希腊之所以独立,腓律宾、图兰斯法耳之所以抗击强敌” ,皆是这种“道德与感情”结合所致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结合”,指的即是“民族精神”。而具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的民族,其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则“皆必有特别之性质”。
,皆是这种“道德与感情”结合所致的结果。这里所谓的“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结合”,指的即是“民族精神”。而具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的民族,其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则“皆必有特别之性质”。 也即在他们看来,具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的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各异,而其所各自具有的“特别之性质”的“民族精神”,则正是各民族之所以立国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
也即在他们看来,具有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的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各异,而其所各自具有的“特别之性质”的“民族精神”,则正是各民族之所以立国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
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搀杂,而不可以灭之也。
放眼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各主要大国,也莫不是以“民族精神”作为其立国的根柢的。其云:
日人知有大和魂焉,德人知有日尔曼祖国焉,法人知有佛郎克大帝国焉,英人知英旗之所在无往非彼族之占领地焉。彼其泣于斯,歌于斯,舞蹈于斯,崇拜馨香于斯者,其心目中恍若有神使鬼差颠倒于其间者,故能游心大宇,发为猛勇踔厉发挥刚毅之气。呜呼!此何物耶?其即吾所谓民族精神云云者耶!夫非民族固有之良耶?
“民族精神”,他们又往往将之表述为“国魂”,如许之衡云:
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泼进取为国魂,美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人以武士道为国魂,各国自有其国魂。
或者又将之表述为“国粹”,如许守微云:
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
“国魂”或者“国粹”,则根源于“国学”。如许之衡曾经即说道:“国魂者,源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 “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之事矣。” 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如果“国学”灭亡了,则意味着其种、其国皆真正灭亡了。其云:
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如果“国学”灭亡了,则意味着其种、其国皆真正灭亡了。其云:
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兰也,皆先变乱其语言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焉。迄今过灵水之滨、瓦尔省府之郭,婆罗门之贵种,斯拉窝尼之旧族,无复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间者,则国学之亡也。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
如果“(国)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 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存立的基础,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存亡,所以,当时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便高呼要进行“国魂”的陶铸,主张保存“国粹”,并致力于“古学”的复兴,企图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揭示出民族生存的微言大义,并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比之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如邓实曾经说道:
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存立的基础,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存亡,所以,当时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便高呼要进行“国魂”的陶铸,主张保存“国粹”,并致力于“古学”的复兴,企图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揭示出民族生存的微言大义,并为本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比之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如邓实曾经说道:
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学者乎!梦梦我思之,泰山之麓,河洛之滨,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如有一二书生,好学信古,抱残守阙,伤小雅之尽废,哀风雨于鸡鸣,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名之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则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
民族主义者由于将一民族所具有的“特别之性质”的“民族精神”,看成是民族存立的大本,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存立的基础,注力于对“民族精神”进行阐扬,所以,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秩序进行重构时,它的一个合理逻辑,便是主张按照本民族所业已开辟的文化方向,进行文化新命的再造,它一方面反对传统主义者之固守传统不变的做法,主张对固有的民族文化进行“刷垢磨光”,另一方面,它又反对欧化主义者所界定的文化走向,他们将醉心于欧化,主张“唯泰西者是效”的人谥之为“奴”。如黄节即曾经这样说道:
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根。慨谓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呜呼!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
在他们看来,由于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其“特别之性质”,这就决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也有其性质上的不同,因此,欧化主义者抹杀各个民族文化性质的差异,采取跟着西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做法,便是不可取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日本政教社派同仁的看法也是完全合辙的。
同日本的政教社派一样,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也都有着良好的西学方面的学养,在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他们虽然反对“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一味模效西方的“欧化主义”,但并不反对“欧化”。李世由认为:“世道衰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缺乏。”
,一味模效西方的“欧化主义”,但并不反对“欧化”。李世由认为:“世道衰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缺乏。” 许守微对于“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曾经作了这样的说明:“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
许守微对于“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曾经作了这样的说明:“国粹者,精神之学也;欧化者,形质之学也。无形质则精神何以存?无精神则形质何以立?” 并且明确地表示:“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
并且明确地表示:“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 这与其日本政教社派同仁也是循着同一理路。他们也主张在把定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吸纳西方文化,不断地丰富本民族文化,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与“民约论”思想,即为其所接受,并将之当作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重要资源。
这与其日本政教社派同仁也是循着同一理路。他们也主张在把定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吸纳西方文化,不断地丰富本民族文化,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与“民约论”思想,即为其所接受,并将之当作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重要资源。 刘师培对于卢梭“民约”思想的赞美
刘师培对于卢梭“民约”思想的赞美 ,许守微对于西方“形质之学”的肯定
,许守微对于西方“形质之学”的肯定 ,柳亚子发出的“民权主义万岁”的呼声
,柳亚子发出的“民权主义万岁”的呼声 ,皆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仪所向。他们将“国粹”与“欧化”二者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
,皆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仪所向。他们将“国粹”与“欧化”二者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 进行“民族精神”的阐扬,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并融化西方文化的有利因子,更好地走上像西方那样的文明之路。在这种思想意旨的驱使之下,他们对传统旧学作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也致力于对西学义理进行阐释,企图“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
进行“民族精神”的阐扬,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并融化西方文化的有利因子,更好地走上像西方那样的文明之路。在这种思想意旨的驱使之下,他们对传统旧学作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也致力于对西学义理进行阐释,企图“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基本上都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坚,除了对于同盟会三大纲领中的“民生主义”有异议之外,他们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忠实拥护者。
。大致说来,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基本上都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坚,除了对于同盟会三大纲领中的“民生主义”有异议之外,他们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忠实拥护者。
通过对于欧化主义思潮进行反思,民族主义者在欧化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的对阵之势中别出的这一新的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思路,带有明显的折中调和的倾向。但是,由于它注意到了“民族精神”对于一个民族存立的重要意义,主张根于本民族固有的独特的内在精神来重建一个新的民族文化秩序,这较之传统主义者与欧化主义者来说,似乎充满了更多的理性色彩,其所具有的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进行重构的思路,似也更具前瞻的眼力。然而,由于它与其所批判的欧化主义者一样,仍然未能脱离斯宾塞式的单线直进的“进化论”学说的轨道,这就使其所持奉的对于社会文化秩序进行重构的基本思路,仍然是以西方式的路向为目标,而徒然地增加了一层“民族性”的底色,并且,也使其进行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运思理路在传统/现代、中/西、精神/形质的二分之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左支右绌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