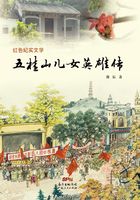
第6章 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在当年中山抗战连天的烽火中,始终活跃着一支与游击队共命运的非战斗系列队伍,这是一支由医生与救护人员组成、被喻作“烽火中的‘白衣天使’”队伍。
战地医院
1939年9月7日上午11时,第二次横门保卫战打响。
当日,一架敌机向张家边方向飞去,经大环村时投下一枚重型炸弹,炸死一名妇女。
8日下午2时,三架战机继续向大环村作轮番轰炸,共投下九枚轻型炸弹,又炸死一名妇女,扬起的巨大沙土当场将一对母子掩埋,后侥幸获救。
10日,敌机再次轰炸大环村,张宝廉家的房屋被炸塌,张宝廉身负重伤,几天后去世。
第二次横门保卫战打响后,驻守中山的广东第一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部在长岗建立战地医院,由政治队员关晃明等负责筹建工作,将长岗五堡乡公所改造成医疗室和伤兵收容站。与日寇开战后,战地医院收容的伤兵逐渐增多,于是在乡公所厅堂左右两侧用木板搭设了两个大通铺,大概能解决20多个伤兵床位。除了伤兵,战地医院内还有支前救护中的群众和妇女队员。
伤兵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来越少。9月14日,关晃明早早赶到石岐、张家边等地办理粮食调拨,当天下午就把1000斤大米从张家边运到长岗。
下午,关晃明继续率领运粮队伍行动,途经大岭村时,被日军的飞机发现并投掷炸弹,运粮队员立即躲进了路边的沟渠作掩护,却见一个村民还在路边慌慌张张,不知所措。关晃明立即将他拉进沟渠,就在此时,日机扔下一枚炸弹,正落在关晃明身边,刹那间,村民无恙,关晃明不幸牺牲。
十天后,第一纵队政训室出版一期刊物《好弟兄》,头版头条报道了关晃明的英勇事迹。
伤兵陆续有来,增至近百名。以女性为主的战时救护队队员纷纷投入到战地医院,参加医护管理工作。没有更多的病房和病床,她们就在桥头村边的尖沙尾树林中开辟了一块空地,利用大树作柱子和床脚,削去多余的枝丫,树冠完全保留,搭起一座绿荫大茅棚。
敌机多次在长岗五堡低飞盘旋、扫射,尽入“白衣天使”眼中,而战地医院却没被敌机发现。
1939年10月7日,石岐沦陷。伤兵和受伤群众大量拥进长岗五堡战地医院,敌机多次跟踪追击,沿途轰炸造成更多伤亡。
第一纵队司令部政训室的女政治队员悉数都到战地医院工作,她们除了担负日常医护工作外,还与战士谈心,做心理疏导。这些女政治队员没有穿军装,但胸前都别有一枚三角形布质证章标式,上有“政治队员”字样。
每天清晨,长岗溪流的两岸最是繁忙。梁秀芳、麦秀等一队“天使”队员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提着脸盆、铁桶来到溪水边,搓洗那满是血污的纱布、绷带,有的还为伤员战士们洗衣服,她们边洗边哼唱着抗战歌曲。
这便是抗战初期,以国民党武装部队为主体、共产党发动群众积极配合所形成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军民共融的动人画面。1940年3月8日,日军再次占领石岐,战地医院才实现了大转移。
除了以石岐为中心的战地医院外,一、二、四、五、八区亦相应成立战时救护队和伤员救助中心,如二区的叠石沦陷前,救护队就集中青岗村待命,救助中心就设在该村的白蕉围一座碉楼中,救护队全副武装,上山警戒。
日寇的飞机从三灶机场起飞,而贴着“膏药旗”标志的轰炸机则在叠石、全禄、新村、青岗一带侦察寻找目标。日寇敌机肆无忌惮地盘旋,然后作低空俯冲,昂头又起,随即从机舱扔下炸弹,尾部射出连串子弹。多间民房当场被炸塌,十余名村民死伤,教护队闻风而动,纷纷奔赴灾区。
敌机仓促投弹后,飞往龙船地一带虚晃一下,马上又折返叠石,继续向灾区投弹,向救护队扫射。
敌机迂回复返,队长杨正矩下令散开,到安全地方隐蔽。此时树下、防空洞、屋檐下已挤满躲避的民众,队员们只好就地卧倒,队员杨丽容找到一处山崖作掩体。来不及离开的村民又被炸死七八人,尸体支离破碎,榕树上挂着炸断的腿和手臂,鲜血染红了一大遍地,惨不忍睹。不幸,一颗炸弹落在杨丽容身旁,塌泥将她全身掩埋。
敌机走后,队长检查队员时发现少了杨丽容,急令分头查找。最后,大家在那座断崖处拼命用手挖,直到将她挖出,发现其身体已被削去一大块,大动脉被炸断,血染黄沙,人已殉难。
在场群众纷纷落泪,战友们悲痛不已,有的更是泣不成声。二区随后召开了杨丽容烈士追悼大会,中山县各界人士和村民上千人参加。人们深切怀念这位勇敢美丽的救护天使,叠石村在杨丽容殉难处勒石立碑作永久纪念。
随着抗战队伍日益壮大,1943年底,中山人民抗战游击队在五桂山槟榔山村举办了两期卫生员训练班,学员50余人,学习优异者被选派到澳门名医招兰昌医生的诊所及镜湖医院深造,为五桂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和其后成立的中区纵队、珠江纵队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
游击队成立初期,伤病员特别多。病者多因营养不良造成夜盲,或因蚊叮虫咬感染疟疾,或因长期赤脚行军造成下肢皮肤溃疡,这三种疾病成了困扰部队战斗力的三大流行病。一次出发夜袭,一个患夜盲的战士看不清路,竟然不慎跌入潭中淹死,令大家悲痛不已。针对缺医少的困扰,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司令员林铿云决心排除这个困扰下令在槟榔山建一个医务所,代号叫“海珠桥”。
建医务所的首要问题是缺乏人才,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周扩源。周扩源曾经跟其父亲学过中医,林铿云马上调他来筹建医务所,然后又调来学过药剂的黄仕芬,以及做过助产士的邓碧瑶。
人到齐了,全部家当却只有一副注射器、一副钳,一些阿司匹林、红汞、碘酒等以及一小包药棉和一小瓶酒精。周扩源马上找到林铿云,诉苦说:“林叔,这一无药,二缺人,让我如何开张呀?”
林铿云听罢大笑道:“没有药,向你父亲请教如何自制。人手缺,我来帮你开一个训练班培养。”
原来周扩源的父亲是八区著名的跌打医生。林铿云马上让人将周扩源的父亲请到五桂山上来,又将已在八区工作的周扩源的妹妹周兰也调到医务所,后来干脆将周扩源的母亲也请来帮忙制药。周扩源父亲的药主要是山草药,碾碎了调以食油或者凡士林,效果不错。
此后,困扰部队的三大流行病总算得到缓解,领导也放下心来。林铿云打听到周扩源父亲的生日,在生日当天特意将周扩源一家找来,对周兰和周扩源说:“今天是你们父亲的生日。他与我同岁,在部队也算得一个老人家了,你们一起陪他吃一顿饭吧。”
周扩源的父亲十分感动,参加抗日工作的意志更坚定了。后来,他被敌人逮捕,遭到严刑拷打,被捆绑多日始终不屈。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马上为周扩源的父亲解开绳索,但他已经无法行走了,他咬着牙,让人搀扶着一步步返回部队。
训练班不久就开办了,学员大多是新参军的年轻姑娘,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她们大多识字不多,一看到药名就晕头转向。除了努力学习文化、分辨药名之外,她们还找到了聪明的辅助办法,一是靠辨颜色:止痛针是黄的,强心针是白的,红汞水是红的,碘酒是黑的;二是靠辨味道,有的药可以用舌头去舔,靠味道分清。她们学习非常刻苦,学注射就找猪肉来练习,有时还在自己身上练习,要找草药,看过标本就出发,翻山越岭实地采摘。
最终,游击队的大队建立了医疗室,区中队配有卫生员、救护队,还在较隐蔽的地方建立若干个伤病站,治疗重病号和伤员,整个游击队的医疗系统也算是健全起来了。
杏林中不少义士、护士加入了这个医疗系统,西医刘帼超便是其一。她十年如一日,为五桂山游击队义诊疗伤,培训医务人员,她的“博爱医局”(“桂园”),被游击队员们亲切称作“后方医院”。
编外医生
中山四区长江乡的陈桂明,早年毕业于翠亨中山县立师范学校,与杨日韶、谭桂明(谭福鑫)、袁世根等是同学。毕业后曾在农村任小学教师,再考入中山著名中医生程祖培(中山县六七十年代人民医院院长、名医程观树的父亲)主持的中山崇正医院讲习所学医。当时学员只有六名,三年为一届。
陈桂明1938年毕业后,在四区大鳌溪乡开设诊所。1942年冬以后,五桂山游击队常在长江乡一带活动。一日,杨日韶、谭桂明登门探访陈桂明,三人一见如故,共话同窗。
陈桂明对杨、谭二人毕业后的前程去向略有所闻,不便多问,却在话语间不时流露出钦佩之言。见及于斯,杨、谭二人自然便扯到部队缺医少药的窘况上来。
陈桂明听罢,心口一拍说道:“若二位信得我过,日后部队上的事便是老同学我的事。凡是指战员有病,请到我诊所就治;若有不便,我还可出诊。如何?”
真是访者有意,主人有心。陈桂明的一番古道热肠,令杨、谭二人大喜,杨日韶说:“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这番助人热心,我和福鑫(桂明)当年早就在学校领受过,来时路上就说起,只是担心会影响你。”
“这是哪里话,你们出生入死都不怕,我‘扶台摄脚’(意为做些帮衬功夫)算什么?”陈桂明毫不犹豫。
“那太好了!”杨日韶拍了拍老同学的肩膀,谭桂明接着补充道:“诊金我们就不客气了,但药费我们日后有条件再补偿好吗?”
“福鑫(桂明)兄这就太见外了,这样吧,你们权当把我当作是你们部队的一个‘编外医生’吧。”陈桂明说道。
此后,游击队员便常到陈桂明的诊所治病,或邀其到部队诊治,他与部队的关系日益密切。其间,陈桂明也参加部队的一些活动,部队上下都亲切地叫他陈医生。
一次,陈桂明到五桂山松埔村开会,被介绍与欧初、吴孑仁等相识。欧初大队长热情动员他参加部队。后来在五桂山区开展建政工作时,他还被选为长江乡副乡长,龙焕容(党员)为乡长。
1943年6月,日军一部和伪军第四十三师共1500人兵分六路从石门、合水、长江、灯笼坑、马溪和石莹桥围攻五桂山区。长江一路的敌人由石岐南门绰号叫高佬钊的人(伪密侦队员)做向导。是日早上,陈桂明早饭后跟妻子黄莲英说去合水口里开会,便骑自行车外出。刚出村口不远,陈桂明就碰上敌人,当即被截查。当时被截查的还有罗元(邻乡的乡长)和一个老头。
敌人搜查陈桂明的全身,搜去驼表一只、金戒指一枚,随后又押着他回家搜查,搜出药书一本。日军认为陈桂明是行医的,正打算放了他。
岂料在场的伪密侦高佬钊认识陈桂明,他附在鬼子耳边指认说:“他,是山坑人。”(山外人俗称欧初部队为山坑人)鬼子立即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大叫,要陈桂明交出枪支和欧初。
陈桂明答道:“我一个医生何来枪支,更不认识欧初。”日军一再威逼他也不说。无奈,日伪军把他们三人一起押到附近的小学。
学校门外有一棵三稔树,敌人将三人捆绑在三稔树上,然后躲入学校饮茶。罗元被绑得松,乘敌人一个不备,挣脱绳索逃走了。陈桂明正要仿效,却被敌人发现,立即开枪。他被打伤了眼睛,顿时血流满脸,昏倒在地。接着敌人又提了一壶开水淋他,把他折磨得不似人样。
受尽严刑拷打的陈桂明头脑依然清醒,咬紧牙关,始终不吐露半字。日伪使尽花样仍无法从陈桂明嘴里掏出半点游击队的情况来,气急败坏地把陈桂明和另一个无辜的老头押到山坑里枪杀了。陈桂明牺牲时年仅32岁。
当年如陈桂明那样为游击队赠医送药的杏林义医不少,陈桂明是他们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很多游击队的“编外医生”活跃在日常行医当中,当年八区的陈爻象便是一例。
陈爻象,又名陈宽怀,八区斗门乾务镇南山新村人。18岁在广州名医黎庇门下笃学中医,学成回乡开设医馆,兼营药铺“天生堂”。
“天生堂”位处村中心,门前用木杉搭一葵顶凉棚,棚内设凳,专供村民闲坐聊天。当年陈培光、陈福、陈勇、陈金等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士曾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借聊天喝茶,向村民宣传抗日,讲救国救民的道理。陈爻象妻子张珍瑞在药铺负责配药,稍有空闲便为大家烧水冲茶。
1941年南山沦陷。一天,日兵突然在新村到处搜寻游击队和抗日人士,正坐在“天生堂”门前的陈培光等人来不及躲避,陈爻象急中生智,一把将他们拉入“天生堂”,让他们各就各位。
日兵冲进来一看,只见有的用铡刀铡甘草枝,有的用铜盅在摏药材,再有的用毛刷刷枇杷叶……陈爻象忙上前比划,意指这几个人都是自己的伙计。日兵见状只好悻然而去。
这几个“临时伙计”正是当时活跃在中山八区的陈中坚游击队的队员。日军入侵南山六里时,陈爻象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以医生的身份穿过日军封锁区(医生有通行证),到禾丰里为驻扎在树林里的陈中坚游击队队员诊病疗伤。
因有不少外伤病员,每次来看诊既要看病,还要为一些外伤队员换药。为防被日军发现不能在现场开处方,陈爻象便将伤病员分成几类病症,回到“天生堂”后让妻子张珍瑞一个不错地配好药,再交地下游击队员带走。配药不是配菜,万不能张冠李戴的,陈爻象从不出差错的医术令人佩服,其不畏风险的抗日爱国情怀更是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