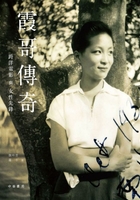
三 桃樂西·阿茲納的故事
1919年,22歲的桃樂西·阿茲納,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在派拉蒙片廠工作。阿玆納的父親在荷李活擁有一家餐廳,她少年時就見過很多舞台和銀幕的明星,在她家的餐廳出出入入,並不覺得他們很神秘。儘管她曾經在南加州大學學醫,但是暑期實習讓她打消了當醫生的念頭。用她的話說,她想像耶穌一樣「救死扶傷,但是她希望可以立刻治療,並且不用動手術或者用藥」。(6)這是阿玆納選擇了電影的理由。她1974年接受訪問時,曾這樣幽默地描述她如何得到片廠的工作:
那是一戰後不久,一切行業都開始復蘇,甚至連嬰兒影樓都紛紛開業。有人幫我約見了威廉·德美,告訴他我是一個聰明的女孩。那時候因為流感讓很多人病倒,片廠需要人手。只要稍微顯示出一些才能或知識,即便是沒有工作經驗的人也有可能獲得機會。(7)
威廉·德美(William DeMille)那時候是製作總管,他建議阿玆納到拉斯基片廠各個部門參觀一下。阿玆納看過威廉的弟弟、大導演施素·德美(Cecil B. DeMille)的拍片現場後得出結論:「要在電影界工作,就要做導演,因為大家都聽導演的。事實上,導演就是整部電影。」(8)這個認識,可以說讓她心裏一直懷着一個目標:做導演。

剛入行的桃樂西·阿玆納。
阿玆納在片廠的前七年一路從抄寫員、場記、剪接做到了助理導演,在獨立執導之前,已經參與了五十多部影片的製作,卻還沒有做到導演的位置。1926年,獨立電影公司哥倫比亞邀請她加盟去做導演,她於是準備離開拉斯基片廠。在離開之前,她覺得已經在這裏工作了七年,應該找一位「要人」談話之後再離開,沒想到談話之後,派拉蒙高層決定留下她,導演A片,也就是高成本的製作。這樣,她的工作條件就會遠遠好過當時規模還很小的哥倫比亞。第二天的報紙上就登出,拉斯基任命女性作導演。不久後,阿玆納導演了默片《艷女新裝》(Fashions for Women, 1927),並且獲得了成功。在此期間,很多訪問阿玆納的記者都驚嘆於她的外形與其他女性的不同,有一位記者這樣寫道:
這是一張很好看的臉,充滿生命力;她的皮膚透明而健康,沒有用化妝品;她的眼睛是深深的藍紫色,長睫毛投下陰影。我不敢去試圖欺騙這雙眼睛。……工作的時候,她穿着剪裁十分合體的花呢西服,一件男式襯衫,打着領帶。襯衫是她向紐約的一家公司成打定製的。她說,只有這身服裝,才適合她在片廠的工作。
很多記者注意到她既沒有剃眉毛也沒有化妝,但是身材嬌小,說話聲音溫和;似乎總是要在她男性化的外表下找到一些女性的特質。拉斯基影片公司後來經過重組,變成了荷李活五巨頭之一的派拉蒙,公司的公關人員喜歡強調阿玆納小姐的片場最有秩序,同時還在宣傳照片中,很樂意展現阿玆納的男性化形象與嫵媚的女演員形象的對比。其實在默片時代,美國曾經有過十多位女導演,其中愛麗絲·吉·布拉舍(Alice Guy-Blaché, 1873-1968)和露易絲·韋伯(Lois Weber, 1879-1939)都是片廠女皇,每人都導演過幾百部短片,韋伯還有二十幾部長片。荷李活完成從默片到聲片的過渡時,因為韋伯已經沒有再導演電影,阿玆納成為名副其實的業界「唯一女導演」;至於後來,她被稱為荷李活「首位女導演」,則實屬媒體健忘。

阿玆納和《艷女新裝》女演員Esther Ralston。

阿玆納在拍攝現場手執寫著她的名字的導筒。

報刊樂於報導阿玆納在片厰從打字員、剪接到導演的故事。
1928年前後,荷李活的電影公司為了保持競爭力而紛紛投資錄音設備,到1930年全美國的戲院基本上都有了音響配備。在有聲片起步的幾年裏,很多默片時代的導演、演員都被淘汰。在默片時代,電影不受語言的限制,靠形體動作和蒙太奇表達故事;進入聲片時代之後,創作的理念和方法都要改變。比如,演員開口說話以後,故事開始要依賴對白,不少帶有口音的演員也被淘汰。阿玆納完成的首部聲片作品《野會》(Wild Party, 1929)再獲好評,這部影片的主演嘉麗拉寶也晉升成一線女明星。阿玆納因為和幾位女演員合作後,都提高了她們的聲譽,而逐漸擁有了「造星者」的美譽。作為荷李活唯一女導演,她奮鬥和成功的故事被多次報導。
麥卡錫:在荷李活早期的聲片時代,只有一位女導演創作過一批重要的作品,那就是桃樂西·阿茲納。她總是在片廠裏,大部分的照片中都穿着男式西裝,打着領帶,梳着很短的頭髮。劇組成員當然清一色都是男性:攝影組、燈光組、電器組自不用說。有時候服裝會是女人負責,還有一個叫「劇本女郎」的職位,負責故事的連貫性幾乎總是女性外,其餘的都是男人。「女人是不可能控制這麼一個劇組的」,這就是當時的共識。阿茲納的男式髮型和男裝,多大程度上是她個人喜好,多大程度上是為了看起來更有權威,我不知道。在女性主義電影評論圈中,她引起了很多興趣,被作為一個特別的個案來研究。
阿玆納早期的導演作品幾乎都獲得了好評,讓她能夠在派拉蒙持續工作到1932年,並在六年之中導演了十部電影。在離開派拉蒙之前,阿玆納經歷了一伏一起,《女職員》(Working Girls, 1931)遭受了評論和票房的雙重失敗,但是年她執導的《寒濤儷影》(Merrily We Go to Hell, 1932)一片,則是當年最為成功的電影之一。(9)因為一系列原因,阿玆納同年離開了派拉蒙,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獨立簽約導演。她獲得的第一個合約,就是導演嘉芙蓮協賓(Katharine Hepburn,凱瑟琳·赫本)主演、雷電華製作的《情天飛絮》(Christopher Strong, 1933)。伍錦霞是否有看過這部電影,不很清楚,但是這部聚焦女飛行員的電影,可能會因為兩個原因吸引錦霞。第一,女飛行員作主角的電影可能會吸引關注飛行的錦霞:她的收藏中有兩張飛行員的大照片,都是簽名送給她本人並祝福她全家的;作為聯合製片和導演,她的前兩部電影的主角包括一位男飛行員和一位女飛行員。其次,《情天飛絮》講述一個成功的女飛行員愛上了一位有婦之夫,阿玆納的電影故事通常都圍繞着「非法」的、不為社會所容忍的愛情與激情;錦霞後來的電影,也在題材上多有應和,一方面批評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低下地位,一方面讚揚女性在追求自由戀愛、民族大義方面表現出的勇氣與犧牲。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玆納脫離派拉蒙、變成獨立簽約導演之後的十年中,她一共只導演了六部電影,其中有五部電影,是在一位男導演不能完成監製的要求時,臨時走馬換將的。這五部電影之中,阿玆納為雷電華執導的《情天飛絮》和《迷樓飛燕》(Dance, Girl, Dance, 1940),以及為哥倫比亞執導的《人去樓空》(Craigʼs Wife, 1936)都獲得不錯的成績,這三部電影現今仍引起女性主義學者最多的討論。在拍攝《蓮娜小傳》(Nana, 1934)和《彈性戀愛》(The Bride Wore Red, 1937)時,阿玆納都在如何理解女主角性格上與米高梅的老闆梅耶發生了很大的分歧,影響了影片的最終效果,造成了後來她提早退出荷李活。阿玆納還為雷電華導演的《迷樓飛燕》,是現今女性主義學者特別熱衷討論的作品。阿玆納告別銀幕的作品是表現戰時女間諜的《亂世英雌》(First Comes Courage, 1943),在拍攝快要結束時,她患上肺炎而病倒了,哥倫比亞安排其他導演完成了她的工作。一年後,她病癒,並決定離開荷李活。她與女舞蹈家瑪儂·摩根(Marion Morgan)同住在加州居所三十年後,摩根病逝。1936年,阿玆納成為美國導演協會第一位女性會員,荷李活的星光大道上有她的一顆星星,表彰她對電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