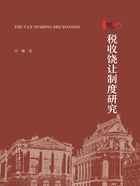
二、主要类型
根据缔约国在协定中所规定税收饶让条款的具体内容,可以将税收饶让制度分为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和固定比例抵免机制。根据税收饶让条款是对缔约国双方都适用还是仅对缔约国一方适用,可以将税收饶让制度分为单边饶让机制和双边互惠饶让机制。根据税收饶让条款是否仅在一定期限内适用,可以将税收饶让制度分为附日落期限的税收饶让制度和未附日落期限的税收饶让制度。
(一)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与固定比例抵免机制
根据来源国减免税收的动因不同,可以将税收饶让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来源国实施税收优惠措施而减免的所得税税收,居民国视同其税收居民已在来源国纳税因而允许抵免居民国税收,所以称为“税收优惠饶让机制”(Tax Incentives Sparing Regime);另一类是由于居民国在税收协定中承诺,将按照固定比例抵免纳税人在来源国所缴纳的预提所得税,而不考虑纳税人在来源国实际缴纳的税额,所以称为“固定比例抵免机制”(Matching Credit Regime)。根据缔约国双方的合意,在税收协定中可以单独采用上述任一机制,也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类机制。
1.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由于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所饶让的是来源国因实施税收优惠措施而减免的所得税税收,因此准确地界定来源国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所能减免的来源国税收,是实施税收优惠饶让机制的前提条件。各国一般会根据国家税收主权独立原则,在国内法律法规中制定各类关于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降低所得税税率,减免所得税税额,允许成本费用的加计扣除,或允许部分收入免税等。于是纳税人取得来源于该国的收入时,可以依据该国法律享受相关的来源国税收减免,即被免于缴纳部分甚至全部来源国所得税。但是若纳税人居民国对其税收居民的全球收入征税,并且采用境外税收抵免法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时,纳税人在来源国被减免的所得税一般将不能在居民国被抵免,除非来源国与居民国在双边税收协定中约定了采用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由于来源国税收优惠政策所针对的对象存在差异,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中约定的税收饶让条款也存在不同文本,因此居民国承诺饶让抵免的来源国税收优惠措施以及所减免税款的范围也会存在差异。
1.1 针对外国投资者,还是针对外商投资子公司
来源国在国内法中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可能仅针对外国投资者、仅针对外商投资子公司,或者既针对外国投资者也针对外商投资子公司。因此居民国在税收协定中作出饶让承诺时,往往对来源国税收优惠措施给予区别对待,例如承诺仅针对来源国一些特定税收优惠措施所免除的来源国税收,适用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例如,根据《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第23条第4款中规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马来西亚政府承诺当马来西亚居民依据中国法律规定的以下税收优惠措施在中国享受了所得税减免时,马来西亚将视同其居民已在中国缴纳了税款,并且允许其在计算马来西亚税收时予以抵免。
《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中所规定的该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对于马来西亚在华子公司是采用中外合资企业形式还是采用独资企业形式,马来西亚政府所承诺的饶让抵免范围实施不同的标准;而且马来西亚在华子公司采取的企业形式,还影响到马来西亚投资者仅能就其自身在华享受的税收优惠适用税收饶让,还是也可将其在华子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也纳入饶让抵免范围。在后者情况之下,显然马来西亚投资者所享受的饶让抵免范围更大,因此从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中获益也更大。所以理论上而言,《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中所规定的税收饶让制度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影响马来西亚投资者选择其在华子公司的企业形式。
(1)当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在华投资设立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时,不仅可以在马来西亚抵免其自身在华享受的税收优惠,也可将其在华子公司所享受的一些税收优惠纳入饶让抵免范围。
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可抵免的将是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2]第6条中所规定的针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投资者的所得税优惠,即“合营企业的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期限不少于五年的,经合营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税款的百分之四十。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此外,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可在马来西亚抵免其在华子公司所享受的以下中国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减免:一、其在华子公司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5条所规定的针对合资企业所得税减免,即对新办的合营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对农业、林业等利润较低的合营企业和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开办的合营企业,按前款规定免税、减税期满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还可以在以后的十年内继续减征所得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二、其在华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3]第3条享受的地方所得税减免,即“税法所说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百分之十的地方所得税,是指按合营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额计算征收。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减征或者免征地方所得税的,由合营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2)当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在华投资设立的是外商独资企业时,马来西亚政府在上述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中所承诺的抵免范围有限,未涉及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在华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而仅限于马来西亚税收居民在华子公司享受的两项所得税减免优惠:一是在华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国企业所得税法》)[4]第4条规定的地方所得税减免,即“外国企业按照前条规定缴纳所得税的同时,应当另按应纳税的所得额缴纳百分之十的地方所得税。对生产规模小,利润低,需要给予减征或者免征地方所得税的外国企业,由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二是若在华子公司是农业、林业、牧业等利润率低的企业,则根据《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条规定可以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即“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等利润率低的外国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按前款规定免税、减税期满后,经财政部批准,还可以在以后的十年内继续减征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税。”
(3)《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中所规定的“本协定签订之日或以后,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同意的中国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法律中采取的任何类似的特别鼓励措施”,为该税收协定缔结之后,缔约国双方继续扩大该税收优惠饶让机制的适用范围预留出了谈判的空间。当中国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且新措施类似于上述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中所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税收优惠和外商独资企业税收优惠时,在获得马来西亚同意的情况下,中国的新税收优惠措施也可被纳入《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适用范围之中。
1.2 针对特定优惠,还是所有税收优惠
有一些税收协定不限制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的适用范围,即对于来源国提供的所有税收优惠措施,居民国在税收协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中都承诺予以饶让抵免。例如,《中国和韩国税收协定》(1994)第23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税收减免,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这种宽泛的适用范围条款较常见于那些采用双边互惠饶让机制的税收协定之中,因为缔约国双方皆可能处于来源国角色,而且往往国内法中都规定了税收优惠措施时需要对方承诺饶让,因此皆有意愿不限制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的适用范围。
但是在实践中,这种不对税收优惠范围予以限制的饶让机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由于来源国在制定税收优惠措施时无须顾忌能否被纳入协定中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条款的适用范围,往往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存在滥用税收优惠和进行有害税收竞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居民国的税收征管成本相对较高,因为需要投入更多的征管资源来查明来源国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以及计算可饶让抵免的来源国税收金额;尤其是当来源国税收优惠措施变动频繁或比较繁杂时,居民国税务机关可能会难以准确、及时地预测出其因承诺税收饶让而将减少的税收收入和投入的征管成本。
也有一些税收协定在采用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时,明确规定仅适用于来源国一些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例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税收协定》(1988)第23条第5款规定,澳大利亚承诺针对中国税法中明确规定的下列税收优惠给予税收饶让:
《中国和澳大利亚税收协定》(1988)中这类明确针对来源国某些特定优惠措施的税收饶让制度,一般出现在仅由缔约国一方(例如澳大利亚)承诺饶让缔约国另一方(例如中国)税收优惠措施所减免征收的所得税额,即单边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之中。缔约国双方通过在税收协定中明确约定饶让制度所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便于居民国测算出饶让抵免的金额,同时也能提高纳税人适用税收饶让制度时的确定性。因此站在居民国立场上考虑,在税收协定中规定此类明确针对来源国某些特定优惠措施的税收饶让制度,往往会对居民国比较有利。
但是站在来源国立场上考虑时,会发现此类明确针对来源国某些特定优惠措施的税收饶让制度会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当来源国废除该机制所约定的某些税收优惠政策时,会导致该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无法继续实施,虽然关于该饶让机制的条款将继续保留在双边税收协定之中。以《中国和澳大利亚税收协定》(1988)中规定的上述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为例,由于其仅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中规定的一些特定税收优惠措施,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废止了上述法律法规时,这些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便无法继续实施,虽然它们继续保留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税收协定》(1988)之中。因此这类针对特定税收优惠措施的饶让机制,实际上给来源国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导致其在行使税收主权去制定或废止税收优惠措施时,将不得不考虑税收协定中税收饶让机制的实施效力。因此,站在来源国立场上考虑,在税收协定中采用一些没有针对性的,或者适用范围比较宽泛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会对来源国比较有利。
为了解决税收饶让机制可能由于来源国税收优惠措施变动而无法实施的问题,一些缔约国在税收协定中规定了变通方法。例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税收协定》(1988)第23条第5款最后一段中作出了以下规定:
根据该条款,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缔结了该税收协定之后,若中国政府修改其税收优惠措施,只要该修改不影响税收优惠措施“总的性质”,则缔约国双方可通过换函的方式,来确定修改后的中国税收优惠措施是否也能被纳入该税收协定中所约定的税收饶让机制适用范围。
再例如,《印度和日本双边税收协定》(1989)第23条第3款规定,日方承诺,印度若将来制定新税收优惠措施或者修改现有税收优惠措施,则在与日本事先对新税收优惠或修改后税收优惠的范围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日本将会饶让其居民在印度因享受新税收优惠或修改后税收优惠而被减免的印度所得税。[5]
又例如,《菲律宾和新加坡双边税收协定》(1977)第22条第2款和第4款所规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针对该双边税收协定签订之后来源国制定的新税收优惠,无须获得居民国的事先同意,就可以被纳入该双边税收协定中税收饶让机制的适用范围。[6]相较于《印度和日本双边税收协定》(1989)所规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菲律宾和新加坡双边税收协定》(1977)所规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范围更宽泛。这可能是因为《菲律宾和新加坡双边税收协定》(1977)所规定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是一个双边互惠的税收饶让制度,由于缔约国双方皆可能会处于来源国角色,都不希望本国在制定税收优惠措施时受到协定的限制,所以菲律宾与新加坡双方能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时达成共识,采用这个适用范围较为宽泛的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2.固定比例抵免机制
在全球现有的四千多份双边税收协定之中,大多数协定在谈判时所参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OECD范本》)[7]或《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联合国范本》)[8]。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制定了自己的税收协定范本。根据《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缔约国双方限制来源国征税权的方式之一是在协定中约定来源国可对股息、利息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预提所得税最高税率。由于税收协定对缔约国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当来源国法律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协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时,来源国可按照其国内法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但是当来源国法律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高于协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时,则来源国可征税率最高应不超过协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
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则是指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中约定,居民国将按照固定比例抵免其税收居民在来源国缴纳的预提所得税,不再考虑其居民在来源国实际缴纳的预提所得税金额。一般情况下,该固定比例抵免机制仅适用于来源国针对利息、股息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等被动型收入所征收的预提所得税。例如,在《中国和匈牙利双边税收协定》(1992)第23条第2款中,匈牙利承诺将允许其税收居民按照20%固定比例抵免为其股息收入在中国缴纳的预提所得税。同时,缔约国双方在该税收协定第10条第2款中约定,对于匈牙利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的股息收入,中国可以征收的最高预提所得税税率将不超过10%。具体的协定条款如下:
(1)第23条第2款第2项:“当匈牙利居民取得的股息,按照第十条的规定,可以在中国征税时,匈牙利应允许从对该居民的所得征收的税额中扣除相等于在中国缴纳的税额。但是,该项扣除不应超过对从中国取得的该项股息在扣除前计算的匈牙利税收数额。”
(2)第23条第2款第4项:“本条第二款第(二)项中所说的在中国缴纳的税款,在任何情况下,应视为是按照20%税率缴纳。”
(3)第10条第2款:“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0%。”
根据上述协定条款,当匈牙利税收居民获得来源于中国的股息收入时,将依据《中国和匈牙利双边税收协定》(1992)第10条第2款,在中国缴纳不超过10%的预提所得税。当匈牙利对该居民境外税收予以抵免时,将有义务依据该税收协定第23条第2款,按照20%固定比例进行抵免。因此,匈牙利税收居民受益于该固定抵免机制,将能保留其在中国实际缴纳预提所得税与匈牙利规定抵免税额之间的差额,从而降低其税收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匈牙利双边税收协定》(1992)中所规定的该固定比例抵免机制,仅针对匈牙利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的股息收入,这就意味着对于匈牙利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的其他类型收入(例如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资本利得、劳务收入等)则无法适用该项固定比例抵免机制。
从上述《中国和匈牙利双边税收协定》(1992)第23条第2款可见,居民国在实施固定比例抵免机制时,不考虑来源国实际征收的预提所得税金额,而是直接按照固定比例给予税收抵免。由于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应抵免的固定比例,因此居民国无须考虑来源国实际征收的预提所得税金额以及来源国是否提供了税收优惠等。所以对于居民国而言,相较于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居民国采用固定比例抵免机制的税收征管成本较低,抵免方法较为便捷。
在实施固定比例抵免机制时,由于固定抵免比例和来源国征税率之间存在下列变量关系,纳税人实际受益的税收饶让税额也存在差异:
(1)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固定抵免比例
很多国家都在国内法中规定,对于非税收居民来源于本国的股息、利息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等被动型收入,该国将行使来源国税收管辖权征收预提所得税。当来源国的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税收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而且后者又低于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时(即:来源国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来源国可按照其法定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此时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从该固定比例抵免机制中获益的金额为固定抵免比例与来源国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之间的差额。
例如,《中国和塞浦路斯税收协定》(1990)第24条第3款所规定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适用于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即缔约国双方承诺:“在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该税额应视为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于是当中国税收居民从塞浦路斯获得股息收入时,将可按照10%固定比例抵免来源国塞浦路斯所得税。根据塞浦路斯国内法律,非税收居民来源于塞浦路斯的股息收入所适用的税率为0,因此中国税收居民在塞浦路斯为其股息收入实际缴纳的预提所得税金额为零。这就意味着,由于塞浦路斯的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税收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中国税收居民将可受益于税收协定规定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虽然在塞浦路斯并未实际缴纳预提所得税金额,但在中国仍可以按照10%固定比例抵免塞浦路斯税收。
(2)协定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固定抵免比例
当来源国的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高于税收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但后者低于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时(即:来源国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且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首先,来源国受到税收协定的约束,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不应超过税收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其次,纳税人可受益于协定约定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在居民国可以按照固定比例抵免来源国税收。
例如,《中国和德国双边税收协定》(1985)第11条第2款规定:“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该利息受益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同时,在第24条第2款第3项中德国承诺:“在适用(二)项的规定时,应抵免的中方税收应视为:1.(二)项1的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2.(二)项2、3的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上述协定条款所规定的情况就是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即10%)低于协定约定的固定抵免比例(即15%)。因此,即便德国国内税法规定的法定预提所得税税率高于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德国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也不应超过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即10%)。此外,德国税收居民受益于协定约定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在德国可按照15%的固定比例抵免中国税收,由此保留固定比例(即15%)与协定约定的来源国可征收预提所得税税率上限(即10%)之间的差额。
3.兼用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和固定比例抵免机制
3.1 缔约双方采用相同机制
一些税收协定既规定了税收优惠饶让机制,也规定了固定比例抵免机制,而且对缔约国任一方处于居民国角色时均适用。例如《中国和马耳他税收协定》(1993)第23条第3款规定了以下税收饶让条款:
在上述税收饶让条款中,第一句规定的是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即“在抵免优惠方面,在中国或马耳他缴纳的税收,按照上下文,应视为包括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而根据该缔约国一方税收优惠的法律规定减征或免征的税额。”该税收优惠饶让机制的适用范围较宽泛,甚至未规定税收优惠措施的制定目的或用途,仅要求应为“法律规定减征或免征的税额”。第二句规定的是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即“在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情况下,免征或减征的任何税额,应视为按照该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总额已缴纳10%的税收。”缔约国双方都承诺,当处于居民国角色时,将按照10%固定比例抵免缔约国另一方(来源国)的预提所得税。
由于上述税收饶让条款同时含有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和固定比例抵免机制,缔约国在实施该税收协定时可能会遇到一个技术问题:针对某些收入,当来源国既提供了税收优惠也降低了预提所得税税率时,居民国应适用何种税收饶让机制?举例而言,对于非居民来源于中国的股息收入,若中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税率为20%,但同时提供税收优惠,将该法定税率降为0%,则根据《中国和马耳他税收协定》(1993)上述税收饶让条款的第一句,马耳他作为居民国时应实施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允许其居民按照20%(即中国的法定税率)进行税收抵免;但是根据上述税收饶让条款第二句规定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马耳他作为居民国时仅需按照固定比例10%抵免中国税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马耳他选择适用上述税收饶让条款第一句(税收优惠饶让机制)还是第二句(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将导致税收饶让金额不同,必然会影响马耳他税收居民的受益程度。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和马耳他税收协定》(1993)中并未给出任何答案。因此,笔者认为应取决于缔约国对该协定条款的解释和实施。一些国家对于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和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发生重叠适用情况,在国内法中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对于没有针对上述重叠情况制定任何具体规则的,居民国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施税收协定时所作出的协定解释将起到关键作用。当然,也可能会产生争议。
3.2 缔约双方采用不同机制
在一些双边税收协定中,虽然缔约国双方都承诺采用税收饶让制度,但是一方承诺的是税收优惠饶让机制,而另一方承诺的却是固定比例抵免机制。例如,在《中国和科威特税收协定》(1989)中,科威特在第24条第5款和第6款中所作的税收饶让承诺包含了两种机制:一是针对来源于中国的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利息收入,实施固定比例抵免81机制;二是针对中国税收优惠下所减免的税收,实施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具体条款如下:
与此同时,中国在该协定第24条第7款中也作出了税收饶让承诺,但所针对的仅是科威特的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具体协定条款如下:
从上述税收饶让条款中可见,虽然缔约国双方都承诺采用税收饶让制度,但在协定谈判中可能会因税收制度差异和利益不同,而最终决定采用不同的饶让机制。因此在适用税收饶让条款时,首先需要判断纳税人的居民身份,然后再根据其居民国所承诺采用的具体税收饶让机制,给予纳税人相应的税收饶让抵免。由于缔约国双方所采用的税收饶让机制不同,对其税收居民给予的饶让效果也会存在差异。
(二)单边饶让机制与双边互惠饶让机制
根据是仅由缔约国一方在税收协定中作出了税收饶让承诺,还是缔约国双方都作出了税收饶让承诺,税收饶让制度可被分为以下两种形式:单边饶让机制和双边互惠饶让机制。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中约定税收饶让制度时,应采用单边饶让机制还是采用双边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缔约国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情况,双方在税收协定谈判中的能力,以及缔约国双方在政治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相似度和差异性等。
单边饶让机制经常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之中。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与OECD成员国所签订的34个税收协定中,有20个[9]双边税收协定约定了采用单边饶让机制,即由OECD成员国单方面承诺饶让中国所减免的税收。例如,《中国和奥地利税收协定》(1991)所规定的就是一个单边饶让机制,即奥地利在该协定第24条第2款第3项中承诺实施以下固定比例抵免机制,而中国并未承诺采用任何税收饶让制度:“(三)为了上述第(二)项的目的,在中国支付的税收应视为是:1.在股息和利息情况下,该项所得总额的百分之十;2.在特许权使用费情况下,该项所得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由于作出单边饶让机制承诺的缔约国一方往往会有税收流失或征管成本增加等顾虑,因此在作出单边饶让机制承诺时经常会对饶让的范围和额度作出明确限定,例如限定对于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固定抵免比例,限定可饶让的来源国税收优惠范围、制定目的、用途等。
能够达成合意采用双边互惠饶让机制的缔约国双方,则一般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或紧密关系。例如,《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10]、《中国和印度税收协定》(1994)[11]、《中国和古巴税收协定》(2001)[12]、《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税收协定》(2006)[13]以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税收协定》(2009)[14]都约定了双边互惠的税收饶让制度。这些缔约国与中国在缔结税收协定时,在贸易和投资水平方面较为接近或者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地理联系等,所以更容易达成合意采用双边互惠的税收饶让制度。
例如,在《中国和韩国税收协定》(1994)的第24条第3款中,韩国和中国都作出了税收饶让承诺,并且所承诺的机制既包括税收优惠饶让机制(即缔约国一方将抵免缔约国另一方“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减免的税款),也包括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即将按照10%固定比例抵免其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其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所缴纳的预提所得税)。具体协定条文如下:
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税收协定》(1985)中,虽然缔约双方都承诺了了双边互惠饶让机制,但饶让所针对税收优惠措施不同。例如,中国在第23条第2款中承诺,针对马来西亚以下税收优惠所减免的税收,予以实施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马来西亚在该税收协定第23条第4款中承诺,针对中国法律规定的以下特定税收优惠,予以实施税收优惠饶让机制:
(三)附日落期限的税收饶让制度
在一些税收协定中,缔约国双方对于税收饶让制度的适用期限设定了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即约定税收饶让制度的适用期限,一旦期限届满,协定中的税收饶让制度将会失效,除非缔约国双方同意延长适用。日落期间一般由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谈判中决定,一般为5年、10年或15年,时限长短往往与缔约国对其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各自税收政策发展趋势等因素的预测相关。特别是在缔结那些采用单边饶让机制的税收协定时,处于居民国一方的缔约国会更倾向于纳入日落条款,以便在日落期满时获得审查和再次决定是否同意采用税收饶让制度的机会,因为日落期后能否延长适用期限一般需由缔约国双方达成合意。
一些缔约国虽然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时未约定日落期限,但在协定缔结之后,可能通过签订补充协定或者换函的形式,再给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饶让机制附加一个日落期限。例如《中国和比利时税收协定》(1985)第23条第1款第2项中规定了税收饶让制度,由比利时单方面承诺实施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并且未对该机制附加任何日落条款:
《中国和比利时税收协定》(1985)生效实施之后,缔约国双方在1996年11月27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关于修订1985年4月18日在北京签订的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和议定书的附加议定书》时,给上述饶让机制附加了一条为期10年的日落条款,即从该议定书生效年度的次年1月1日起,该固定比例抵免机制的实施期限将为10年。具体条文如下:
经上述议定书修订之后,比利时在《中国和比利时税收协定》(1985)中所单方面承诺的固定比例抵免机制将不再被无限期地予以实施,而是从议定书生效年度的次年1月1日起,被限定了一个为期10年的实施期限。虽然缔约国双方在该议定书中写明“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可相互协商延长该期限”,但议定书所规定的10年日落期限届满时,并未见缔约国双方达成合意延长固定比例抵免机制的实施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