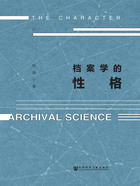
第一节 研究动因与意义
一 研究动因
中国档案学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虽然理论体系略显单薄,但现在已经屹立于中国学科之林,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
在8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档案学建立起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学者队伍逐渐壮大,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档案学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惑,比如技术化对学科发展的挑战与应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把握,基础理论研究的层次如何提升,应用理论研究如何更接地气,政治行政力量对档案学有何影响,社会力量的壮大对档案学的影响,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更新与完善等,类似这些问题一直或者正在困扰着中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
胡鸿杰认为,中国档案学“没有真正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成长模式,没有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档案学人对自己生存的环境认识不足,对档案学自身的价值缺乏恰如其分的评估”[2]。可见,探讨中国档案学的生存环境和自身价值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选题之时,笔者一直在思索中国档案学的生存环境以及自身价值问题,思考到底是什么元素在支撑或影响着中国档案学走到今天,思考这种元素与中国档案学有何内在关联。经过文献梳理和思考,笔者注意到了一个中国档案学界频繁提及的元素,也是中国档案学界在很多时候无法绕开的元素,它就是政治行政元素。政治环境是中国档案学生存发展的主要外部环境,同时政治行政与中国档案学的自身价值有着天然的关联。于是,政治行政元素就成为本书写作的研究起点。
谈到政治行政元素,首先有必要简要分析一下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在政治学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极其复杂,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证明和检验。从区别来看,政治在目前学界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一般指“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3],主要涉及一些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事项;而行政是“行政机构按照法律规定对国家和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以便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达成社会目标”[4],主要涉及一些个别和细微事项的活动。简单来说,政治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而行政就是国家政策的执行。从两者的联系来看,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互为背景,互为基础,政治主导行政,行政从属于政治,行政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为了避免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行过多纠缠,不再对两者进行过度区分,在后文中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称谓。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量的档案都带有天然的政治行政基因,而档案学是一门研究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学问。因此,档案的重要价值——资政辅政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档案学研究中,从而使中国档案学研究或多或少地带有政治行政烙印或个性。从历史上看,中国档案学孕育、创立、发展与繁荣的过程无不与政治行政存在密切关联。在古代政治控制学术的环境中,中国档案学思想就已萌芽,但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基本被政治权力所掌控,为专制统治服务;到了近代,中国档案学的产生更是与政治行政力量有着先天的关联,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运动”是催生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地位得到官方的确认,档案学迅速发展壮大,同时档案学的政治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过分拔高以致最终威胁了自身的生命;改革开放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推动档案学恢复与繁荣的重要因素,随着政治与社会的不断改革和转型,各种类型的档案大量涌现,档案和档案馆成为国家、社会与公众利益博弈的工具和平台,诸如政府信息公开、民生档案建设等档案现象日渐得到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可见,政治行政元素与中国档案学研究存在密切关联。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人的政治取向与行为、档案的政治行政个性以及政治环境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档案学形成了一种政治性格。这种政治性格是中国档案学与生俱来的,并且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它有时凸显在学科表层,有时又隐藏在学科深层,有时得到强化,有时又被忽视和削弱,但这种政治性格始终存在并影响着中国档案学的成长与发展。
因此,分析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似乎也抓住了中国档案学生存环境和自身价值的关键,而且也为探讨中国档案学的许多科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如何评价?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如何完善和发展?这些问题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也是本书的研究动因。
二 研究意义
性格的视角可以为研究中国档案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可以为解决学科发展困惑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分析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有利于档案学界更好地反思学科自身、认清学科生存环境,对于增强学科现实关怀、探索学科未来走向至关重要。
(一)探讨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对学科个性的复归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档案具有重要的凭证作用,档案的原始性、凭证性特点赋予了档案一种强大的影响力。马云在阿里巴巴技术论坛上曾说,“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5]。档案一般与政治行政机构有着天然的关联,何鲁成认为,“档案管理之主要目的在供行政之参考,副目的在保留文献,欲求上述二目的之达到必须注意庋藏”[6];吴宝康认为,“古老的或较古老的档案定义或解释往往更特别突出国家机关在公务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恰好表明档案从古以来在古今中外的国家中首先都是国家和政治机构的活动中产生和出现的”[7];胡鸿杰认为,“文件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公务文件,即公文”[8]……档案与政治行政有着天然的关联,具有浓厚的政治行政色彩,而中国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学科,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行政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其学科发展带有鲜明的政治行政个性和特色。因此,探讨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对其学科个性的复归。
(二)探讨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学科生存环境
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发展环境十分复杂,胡鸿杰认为,应当注重研究档案学的生存环境[9],高大伟认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面临着以政治环境和行政环境为主的“环境困境”[10]。外部环境特别是政治行政环境对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影响至深,该选题有利于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剖析,厘清学科与政治行政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探讨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有利于更好地正视与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政治行政困惑
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政治行政基因是与生俱来的,它与政治行政权力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当今中国档案学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与政治行政的关系。高大伟认为,政治行政因素的变化伤害到了学科的自身价值,研究者出现了“思想的空白或混乱”[11];周林兴认为,档案学人在处理学术研究与行政的关系时产生了一些“角色冲突、失落与失调”[12];徐欣云的观点则与两人不同,认为学界不可过分脱离政治和行政,将档案学定位为管理学科,“仅仅关注信息管理技术和方法并非档案学所长”[13]。可见,如何处理档案学科发展与政治行政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理论困惑,是摆在中国档案学人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是对该问题的直接观照,对于学界正视与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四)研究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为学界探讨学科元理论、反思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档案学界出现了一股对于档案学研究的反思热潮,其中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残留着苏联模式的深刻痕迹,体系陈旧,结构单一,对于新的理论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有学者指出其原因在于封建主义和“左”的影响,自我封闭,理论脱离实际,缺乏学术民主等[14]。不难发现,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行政因素无法脱离干系。因此,严肃地梳理与讨论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可以为学界反思自我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利于推动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自觉。
胡鸿杰认为,中国档案学缺乏一种“支持其理论发展的基础和终极理念”[15],这是造成其学术地位难以稳固的根本原因。本书所讨论的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或许是一次对“理论发展的基础和终极理念”的尝试性探索,其目的在于发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形式,希望这种探索能够为中国档案学元理论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