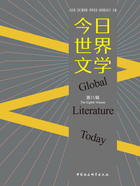
世界文学理论研究
星丛化世界文学[1]
黄峪
【摘要】本篇文章旨在为将星丛范式运用于世界文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文章第一部分对“星丛”这一概念在天文学/占星学、认识论和文学阐释学中的使用做出跨学科考察;文章第二部分对当前世界文学研究中认识论转变做出理论探究;文章第三部分详细说明星丛化世界文学如何围绕三个关键因素进行运作,即不同出发点(points of departure)、视域转换(horizon changes)和普世诗学(universal poetics);最后,作者认为星丛化范式不仅是有益的理论工具,还能为面临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危机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解决之道。
【关键词】星丛范式;世界文学;阐释学;东西方文学研究
Constellating World Literature
Yu Huang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lay the theoretical groundwork for the constellation paradigm i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The first section conduct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nstellation in astronomy/astrology,epistemology,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The second section presents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for an epistemological alteration in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The third section illustrates how constellating world literature operates with three key factors,i.e.points of departure,horizon changes,and universal poetics.Finally,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onstellation paradigm serves not only as a useful theoretical tool but also as a remedy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under the threats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Key words:Constellation paradigm;World literature;Hermeneutics;Literary studies East and West
如果世界文学成为可能的那一时刻终于到来,那么它也将同时、彻底地变为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对这种不可能有所体认。
——艾田蒲,“是否应当重新审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直是众多比较文学学者倡导的理想。[2]这一概念暗示着文学间存在亲缘性和普遍价值,是文学研究的基石[3];并且意味着文学研究从单一国族视野到承认和重估文学多样性的转变。[4]在现代语言学会(MLA)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等专业协会的支持下,许多学者在世界文学集册编选和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在一份关于现代语言学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标准的十年报告中,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追溯了自1950年以来比较文学的转变,新的后战争时代下的跨国族视角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文学研究转而开始关注国族和语言身份。但是,这种新视角对比较文学提出了三项重大挑战,即比较文学研究的精英化、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增多,以及较共时性研究而言重历时性研究。针对这三项挑战,伯恩海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引入新的阅读方式;用跨学科、跨文化的议题拓展研究的疆域。[5]四届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以喧哗的众声(multivocality)体现了德国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差异和非差异的同一(unity of difference and nondifference)。[6]对于苏源熙(Haun Saussy)而言,歌德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分配策略(distribution strategy),而非一个学术领域或一套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7]与其寻找合适的对象(object),比较文学学者应当重新关注领域内的不同项目(projects),后者使得多种多样的对象得以相遇。[8]在这个以单极化、不平等、学术机构转型以及信息化为特征的时代里,比较文学系的愿景与使命应当是跨学科的“将对某些议题的侧重转化为一种理性(rationale)的努力,解释学科内部的讨论究竟关乎什么内容”[9]。
过去的二十年里,以不同路径分析世界文学的学术研究日益增多,但都遇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如果采取一种世界主义而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文学世界”将包含体量过于巨大的文学文本,从而变得难以把握。在国际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文学的自主和平等尚未实现。试图将文学作品按主题进行分类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失去历史的维度。[10]对于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而言,书写世界文学的历史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为世界文学下定义、设计书写方法、确定书写目的。这些挑战源于世界文学的突出特点,即“它的多变性:不同的读者会着迷于不同的文本构成的星群(constellations of texts)”[11]。世界文学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使得文学作品呈爆炸式增长——文本无穷无尽、无从把握,并且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文学(global world literature)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历史可供书写。为这样一种世界文学书写历史意味着要扩大范围,提供“一种类型学(typology)而非一种历史叙述”。达姆罗什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型,这是一种“双重的努力”(a double enterprise)——模型为读者提供有效纵览与宏观框架,读者可以在其中填入自己选择的文学作品。这一做法已经被牛津大学的苏美尔文学电子文本语料库(Electronic Text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证实确实可行。[12]
在讨论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策略时,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提出了星丛范式(constellation paradigm)——“在创作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去甚远的不同文学作品中寻找共性、发现规律”[13]。这是一种基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复合策略,其目标是“寻找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技巧和流派的集合;对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奉为经典,或者当下正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寻找它们的家族相似性”[14]。汤姆森还提出布罗姆(Harold Bloom)著作中实际上使用的模式就是星丛范式,“围绕十个不同的主题集合,将不同时期和文化的作者集结在一起”[15]。汤姆森从这种实验性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中总结出了四项优点:实际、创新、多元、给人以教诲(didactic)。实际指的是能够从流派、形式、作者和作者作品(works within authorships)等多个层面选取经典文本;创新指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能够跨越流派、国族、语言、年代,在相去甚远的作品中找到连接点,用一系列特征定义作品之间的联系;这一范式从两方面体现出多元的取向,其一是它在国族和国际两个层次联结起经典化程度不同的文本[16],其二是它提供了一种颇有前景的阅读模式,可以与其他范式产生互动,从而允许多元的阐释方式;从教学方面看,运用这种范式,教师可以将世界文学呈现为有着诸多历史细节的世界文学系统,而不再只是依照一系列重要作品的书目。[17]在运用星丛化策略图绘世界文学时,分析者必须首先承认“世界文学分化为当代文学(contemporary)和经典文学(canonical)这一正在进行的过程”,舍弃“固执的、浪漫化的将作者视作天才的观念”[18]。
要进一步探究星丛范式,就要回答三个问题:(1)将星丛化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是什么意思;(2)与其他分析手段相比,这种范式有什么特点;(3)它对于世界文学研究有什么优势和意义。这篇文章旨在为将星丛范式用于世界文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文章第一部分对“星丛”这一概念在天文学/占星学、认识论和文学阐释学中的使用做了一番跨学科的考察;文章第二部分对当前世界文学研究中认识论的改变做了理论探究;文章第三部分详细说明了星丛化世界文学如何围绕三个关键因素进行运作,即不同出发点(points of departure)、视域转换(horizon changes)和普世诗学(universal poetics);最后,作者认为,星丛化范式不仅是有益的理论工具,还能为面临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危机的世界文学研究提供解决之道。
一 理解星丛:占星学含义和阐释学辩证法
对于星丛的观察和解读,属于现代学科划分中天文学的范畴。占星学(astrology)[19]在硬科学和人文科学间摇摆不定,被普遍认为是一门“弹性(resilient)学科”[20]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1]。古代占星术可追溯至第一个千年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祭司们最早绘制出十八个星座的星图作为推测季节变化和星体运动的参照点。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古巴比伦的占星师们形成了一种技术和哲学工具——将黄道划分为360度,以便更加准确地呈现行星系统。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绘制了黄道十二星座,并创造了关于十二星座的神话。[22]在之后的时间里,除了对部分星座的命名存在争议外,西方占星术[23]大致沿用了希腊化时代黄道十二星座的划分及其拉丁名称,如白羊座(Aries)、金牛座(Taurus)、双子座(Gemini)、巨蟹座(Cancer)等。[24]
我们可以将占星术中的星座划分与文学经典化(literary canonization)进行类比。[25]与个人观星者颇为相似的是,普通读者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描述的那样,是“为了个人的乐趣阅读,而非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观点”。伍尔夫认为,读者的想法和观点可能“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们仍然“能够促成很重大的结果”。[26]与个人读者不同,文学评论家需要回答诸如定义对象、对比体验、评判价值这样的根本问题。[27]对纪廉(Claudio Guillén)而言,这种认识论上的困境来自“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张力”,或称“同一性与多样性之辩”(debate between unity and multiplicity)[28]。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涉及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其在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中有所体现:庄子告诉惠子他知道鱼的快乐,而惠子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因为做出这番断言的并不是鱼自己。张隆溪认为这次辩论体现了知识的相对性,迁移到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当反思性地理解差异,避免对“真实性”(authenticity)和“他异性”(alterity)进行机械的二分。[29]
怀疑主义与知识的辩证关系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28年发表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30]《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德文标题为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31],后文称《起源》)中也有所讨论。本雅明发现,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戏剧,德意志巴洛克戏剧被否认“与历史有所共鸣”,因为“不管是德意志传奇还是德意志历史,它们在巴洛克戏剧中都没有一席之地”[32]。他接下来说道,“由于受到诸多偏见的影响,文学界注定不能对巴洛克戏剧做出客观的评价”[33]。本雅明所做研究的目的在于,“从一开始就放弃对于整体的把握,保持一定距离观察对象”,从而找到德国巴洛克悲苦剧独有的艺术特征。[34]在《起源》前言中,本雅明使用了“星丛”(constellation)这一隐喻来解释“对于真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the truth)[35]是如何进行的:
理念(ideas)之于对象(objects)正如星丛(constellation)之于群星(stars)。这首先意味着,理念既不是对象的概念(concepts)也不是对象的法则(laws)。理念不增进对于现象的知识,对象也不能作为评判理念是否存在的标准。现象之于理念的意义仅限于作为理念的概念要素。诸现象依其存在(existence)、其共同之处、其差异决定着包含着它们的概念的范围和内容。但现象与理念的关系却截然相反,是理念——对于现象,或说对于现象的要素的客观阐释(objective interpretation)——决定了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理念是永不过时的星丛,各要素可被视为星丛中的点,现象因而被细分,同时也被解放出来。概念的作用就是使这些要素从现象中显现出来,如此,这些要素因在非常极限的状况下而显得尤其清晰突出。[36]
在上述引文中,本雅明使用了“星丛”隐喻来说明“理念”(idea)与“对象”(objects)和“现象”(phenomena)[37]的关系。根据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理解,本雅明的“理念”结合了柏拉图式的“理念”(Idea)隐喻和语言实在论,指的是“实体中的那个瞬间(that moment in the substance)和一个词的存有(being of a word)”[38]。本雅明对星丛隐喻性的使用提出了一种“柏拉图—莱布尼茨式的方法”,用于解决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哲学问题:“何以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general)和普遍化的(generalizing)处理艺术—文学对象的方法,而艺术—文学对象明显是特殊的。”是否有可能摆脱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空洞的教条,同时又忠于时代的特殊性,甚至忠于作者作品中难以再次经验的部分?阐释者能否“外在于”(outside)自我和所处的时刻进行阐释?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是认识论问题,因为其涉及知识的对象;第二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因为其回应了实证主义唯科学论(positivist scientificism);而第三个问题挑战了知识生产者作为观察者或阐释者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以上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缩小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差距?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此处使用了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cal circle)来说明人类理解过程在时间顺序上的整体性:“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所注目的各项事物的重要性时,或说当我们意识到各项事物是如何相互关联时,理解才会发生。”[39]
在阐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时,本雅明使用了第二个隐喻——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本雅明强调了单一理念与相互关联的复数理念的区别。作为单数时,理念从三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一个单子。第一,它是整合的(integrated):“每一个理念都以某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包含着其他所有理念。”[40]第二,它能够容纳表征:“现象的前稳定状态下的表征就位于理念中,正如其在对现象的客观阐释中。理念的层级(order)越高,表征就越能完美地包含其中。”[41]第三,理念是无所不包的(all-inclusive):“每个理念都包含着世界的图景(the image of the world)。”[42]作为复数时,理念指的是包含(incorporate)了现象并且在功能上成为现象法则的“现象客观、实质上的安排(objective virtual arrangement)”[43]。本雅明在悲苦剧(Trauerspiel)中找到了这种整合的相互关系。悲苦剧作为一个整合的、包含性的单子与“文艺复兴悲剧”(renaissance-tragedy)、殉道者戏剧(martyr-drama)和中世纪宗教戏剧等历史上其他戏剧类型有着共同的特性。[44]尽管悲苦剧与其他悲剧类型相互关联,本雅明也指出悲苦剧明显根植于历史,而悲剧则源于神话。两者在形式元素(formal elements)方面还存在很多差异,例如,悲苦剧中的合唱更加繁复,但是相较悲剧,与剧中人物的行为举动关联更少。[45]
在论及历史(history)和时间性(temporality)之间的张力时,本雅明区分了起源(Ursprung)和形成(Entstehung):“起源一词不是指存在者开始出现(come into being),而是指在变化和消逝过程中存在者的浮现(emerge from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d disappearance)。在形成之流中,起源就是一个旋涡,将用以形成过程的质料卷入涡流中。”[46]本雅明坚持认为,历史不应追溯起源,而应揭示理念的形构(configuration of the idea):
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有关起源的学说,是从最极限的状况和明显过剩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理念的构成——即全体有意义的极限状况的并置。在一个理念所包含的所有极限状况被彻底探索之前,一个理念的表征就不能说是成功的。[47]
通过使用星丛隐喻,本雅明阐明了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中时间性和普遍性间的复杂关系。对斯坦纳而言,本雅明运用星丛隐喻具有方法论意义,“对于过去作品的重估能够增进我们对于未来的了解”,因为他展示了“对于巴洛克的研究不只是对古籍、档案的爱好:它反映、预测并且帮助我们理解黑暗的当下”[48]。吉洛克(Graeme Gilloch)认为本雅明使用星丛隐喻不仅“表明了通过概念将现象模式化(patterning of phenomena)的重要性,也指出了这一过程的特点”。这一过程“转变了我们对于现象的理解,这种转变在瞬间发生且不可逆转,那就是现象既保有自身的完整性(individual integrity),也具有相互之间的关联性(mutuality)”[49]。换言之,虽然它们在时间、空间或文体风格上有所不同,每篇文学作品或每种文学类型都相互关联。
二 对世界文学研究认识论转变的呼吁
大约四十年前,艾田蒲提出问题,讨论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否应该在20世纪有所改变。艾田蒲作此建议的前提在于,世界文学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调整思路的机会,呼应歌德认为世界文学是追求文学整体之美,批判各类民族主义的重要观点。更进一步而言,艾田蒲指出,如果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被理解为各种国家文学之总集的话,实际上指称的也就是一种没有任何形容词的“文学”。要研究这个兼容并包的主题,也就等于说是要对这个宏观大类中每篇文学作品开展独立的历史、社会或批判研究。与此同时,还需要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方法(comparatist method),其中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次学科研究,比如说比较文学历史、比较文学社会学、类型理论、美学理论、文学研究等。在此意义上,比较文学可以做的,就是推进世界文学的理念,而非与其类同。为了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学者们应该对自己的局限有所了解,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50]
近十年来,有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呈现世界文学系统的整体状况,也采用了新的分析方法来编撰世界文学历史。达姆罗什撰写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名为《什么是世界文学?》,其中就给出了关于世界文学定义的三重描述,尤其强调此概念的动态发展:
第1,世界文学是国家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第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增益的书写。
第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文本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让我们能够以超然姿态参与自己时空之外不同世界的一种形式。[51]
在以上的第一点定义中,达姆罗什对“国家”(nation)概念进行拓展,从领土主权拓展到在地与民族的形构。他用双重椭圆形折射这个科学意象来描述任何一篇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互动跨文化协商过程,还借用了《怪医杜立德》(Doctor Doolittle)故事中的双头动物“普斯米普育”(pushmipullyu)来描画这个多元文化协商互动的过程。第二点定义基于文学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特点。部分具有高度语言文化可译性的在地化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而其他作品则无法进入国际读者视野。与此同时,文学文本的流通也取决于译者的阐释角色和读者的互动反应。以上这两点意在通过将这些文学作品放置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群组中,以此巩固世界文学的概念,从而使其得以超越跨文化与跨语言界限,保留文学作品的普世价值。而第三点则引入了时间因素,使得以上这两点所构成的定义更为动态。达姆罗什这样写道:“在任何时间,都会有一批数量时有增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某种文化中积极流通,这批作品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被广泛分享,被誉为经典,但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组,任何群组中的不同个体,都会创作出独特的作品集合体,将经典著作和非经典著作融合成实质上的微经典著作(microcanons)。”[52]这种状态与物理学布朗运动过程中分子的随机漂浮极为相似,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模式对此运动状态进行描画分析。为了分析世界文学作品在不同层面上的互动,达姆罗什建议读者阅读外国文学文本时采用超然姿态参与(detached engagement)的策略。作为读者,我们能够以世界文学作品的时空“起源”(origin)为出发点,从一定距离之外观察自身,正如达姆罗什所说:“将我们自身现状与我们身边和之前出现的大量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相连,构成三角并置关系。”[53]他在此书结尾处,绘出了一幅图画,描写的是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时,随军的法国科学家测量埃及吉萨金字塔的大斯芬克斯像的场景。在达姆罗什看来,这幅图画表征着“定位既非当下,也非在古代埃及的一段历史”,也正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代表着打开了一个世界文学的世界:这曾经是在历史和地理意义上都有所限定,相对更为欧洲化和男性化的领地,而现在则变成一片更为辽阔与新奇的疆域”[54]。在这本书中,达姆罗什指出世界文学或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和规模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此书未对时间多样性所带来的重要范式转换作进一步探讨。
卡萨诺瓦撰写了一部关于世界文学共和国的研究专著,影响深远,她试图以此“带来一种视角变化:‘从某个优势定点’来描述文学世界;也展示这个奇特庞大文学世界的各种运作规则,这个世界充满竞争、挣扎与不平等”[55]。她意在“重新建立文学、历史与世界之间失落的连接,但也保存每篇文学作品无法整齐划一的独特个性”[56]。她并没有处理世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世界文学空间”(world literary space)一个协商之地——“一个平行领地,和政治领域相对独立,生成于某种文学特质的相应问题、辩论与发明”[57]。这种文学空间存在的证明首先是诺贝尔文学奖遴选过程中的“国际文学祝圣”,这被认为是一个“为了定义文学普世性而设计的实验室”[58];第二个证明就是对文学时间的特定测量方式,比如说,对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评估已经成为文学评论中的运作机制。在这种审美时间的斗争之中,某些文学作品被归入陈旧或“过时”之列,而其他作品则超越时间淘汰,被尊为经典。[59]世界文学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来说,文学空间中的不同事件并非取决于政治—经济权力关系,例如欧洲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并非完全一致,拉美文学作品蓬勃兴盛,而该地区经济尚待发展。另一方面而言,这个文学空间仍被语言、文学与政治这三个主要形式主导。[60]通过揭示世界文学系统中不平等权力关系,卡萨诺瓦指出文学研究实践很有必要做出改变。正如罗尔(Sarah Lawall)指出,在大多数的世界文学教学模式中,都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格林尼治时间,以此划分所谓的“西方和其他地方”框架。而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关于其他地方的理解,也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和边缘地区有着不同的概念”[61]。
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讨论他对世界文学的构想过程中,描画了“形式的物质主义概念”[62],并提出文学历史的三个抽象结构模式。[63]他也建议应该转换概念,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问题(problem),而非某个特定对象(object)。莫莱蒂重新审视了涵括世界文学庞大整体的各种尝试,也对研究此文学体系的意义进行了反思。他引用了韦伯(Max Web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议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视为另一个类型,关注不同问题之间的概念相连关系,而非各种实物之间的具体关联。在此意义上,莫莱蒂进一步阐明,世界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新范式的起点:“……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象,它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需要用全新批判方法处理的问题: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解决它。这并不是生成理论的方式,理论的生成需要一次跳跃,一个赌注——一个假说,才能起步。”[64]莫莱蒂进一步表明,文学运动发展取决于三大变量:某种文学类型的潜在市场、其整体形式化过程及其语言运用。[65]与此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将比较文学视为一面我们观看世界的镜子”[66]。为了研究文学历史,莫莱蒂建立的三个抽象模型是“统计图形、地图和树木这三种人工造物的三合一,其中文本现实经历了精心计算的简化和抽象过程”。在莫莱蒂看来,这三个模型恰好对应于三个学科,而这些学科“和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互动关系:统计图形对应量化历史,地图对应地理学,而树木对应进化论”[67]。
三 星丛化世界文学:不同出发点、视域转变与普世诗学
与以上提到的不同分析理论相比,星丛范式提出可以对翻译中的世界文学采取一种另类的“行星思维”而非“地图阅读”。[68]这种范式也为应对在编纂世界文学历史中出现的三个挑战,也就是定义、设计与目的[69],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那么,要撰写一部世界文学历史,就是要拓展规模,提供“一种类型学,而非一段历史”。[70]正如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所说,“一种兼具学术性与合一性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语文学”[71]会“对时髦的智性发展浪潮采取开放独立的合宜态度”,从而整合“历史和与文学研究”。[72]要编写这种历史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范式,使得“在地与普世,单一与众多之间的对话可能发生,而这种对话从生成之日直到此时都能够使出类拔萃的比较研究焕发生机”[73]。
在我看来,世界文学星丛范式通过三组要素运作:第一,不同出发点(points of departure),预设了不同世界的多元维度;第二,视域转换(horizon change),在文学作品的流通和翻译过程中得以实现;第三,普世诗学(universal poetics),也就是超越时空限制,令跨文化理解与沟通可行的共同主题与价值观念。
在苏源熙看来,开展与世界文学相关的对话的潜在危险,在于“平面化”(platitude),而这种平面化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平庸性,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扁平性,“也就是说,认为文学能够被地图化为二元维度,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平面,通过这种做法来提炼文学最为重要的特质”[74]。苏源熙的见解和歌德的观点相似,后者认为“对一个有限环境的生动诗意描述将某种特定之物(‘ein Einzelnes’)提升为一种虽有限但亦无穷的宇宙(‘All’),因此我们会相信自己能够在一个狭小空间中看到整个世界”[75]。在这里,“世界”(world)有两层不同含义。一方面,它可能指代的是不同的文学世界系统,其中包括象征意义资本与制度化市场上进行的文学生产、流通与经典化过程。[76]另一方面,它也生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宇宙,或者说是一种普世性的诗学,其中包含“关于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与组成部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并非世上不同传统中所出现的全部批判性观点的无限无穷无法掌握的整体集合”[77]。这里提到的各种文化在地性(cultural localities)也在歌德小说《威廉师傅的旅游年》(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1829)的尾声中有所强调,歌德认为“家中虔诚”(house piety)为“世界虔诚”(world piety)奠定了基础,普世性(the universal)从而被奠基,也必须与在地性(the local)相互渗透贯通。[78]
通过强调不同的出发点,星丛范式可以处理平面化的问题。不同研究者可以从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首先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个“出发点”(Ansatzphänomen),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对此问题的预设倾向”。[79]然而,研究者也不应该将自己只限于这个立场,因为如果要找到“一个部分能够被理解,有所限制并切实存在的现象”[80],就需要采用几个不同的出发点。对于奥尔巴赫而言,一个好的出发点必须具有这样的特质:“切实、准确,有潜力构成一个能够提供更为开阔视野的向心放射圈(centrifugal radiation)。”[81]奥尔巴赫强调,在地文化和语言对于构成切实的出发点尤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语言家园是地球:它不再是国族。语文学家最为珍贵,无可替代的财富仍然是他自身国家民族的文化语言。”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周作人1923年为同乡大白先生的诗集《旧梦》所写的序言,其中提到普世与在地的互通之处:
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 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褊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这虽然是不得已却也是觉得可惜的。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如我们因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no)一般。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文学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82]
通过运用星丛化范式,博览群书的读者能够跟从观星者的步骤来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星丛。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读者能够提炼出一套共同的主题,从而构成他们独特的参考支点,以此从自己的出发点来辨识出不同的星丛。与此同时,这样的观星之举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自己的家乡文化与生活经验。举例说明,廖炳惠对台湾小说家王文兴的现代主义作品《背海的人》(下集)进行分析,提出四种形式的现代性:第一、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第二,单一的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第三,多元的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第四,压迫性的现代性(repressive modernity)。[83]
即使出于不同历史背景,东西方文学研究者对于世界文学的各种讨论观点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那就是文学价值在于超越地理、政治、语言或意识形态界限而对人类进行普世性表征(universal representation),而这种跨文化的普世性也能够从多极文明中总结归纳得出,免于以国族名义或以任何想象的、或者历史上存在的狭义共同体之名义被统一化。这种世界文学的本质与理念存在于其普世诗学之中,这种普世诗学“必须具备可比性,涵括超过一种国族或地区传统,也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84]。这种世界文学诗学所包含的“世界精神”(weltzeit)是这个经典化过程的指导原则。由此,星丛范式呈现出本雅明《德国悲苦剧起源》中所讨论的普世(universal)与特一(particular)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世界”象征着同一性(unity),正如钱钟书所言,“同时之异世,并在而歧出”。[85]这并不能仅仅用“时代精神”或者“地域影响”来草率概括: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覩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氾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知同时之異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異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86]
星丛化范式能够有效地统合世界文学的维度性(dimensionality)和普世性(universality),大量的文学作品能够被视为不同天体的总量集合,其中部分作品受到其同代读者的认可,被视为最为闪亮的经典作品,部分作品在后世评价过程中逐渐获得经典地位,而部分作品则从未进入读者视野,也无从成为经典。在此意义上,这种范式对世界文学[87]项目设计与教学策略也大有裨益。派泽(John David Pizer)在教授“现代世界文学导论”课程中采用了一种原理论的方法,并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平衡普世与特一两者关系的辩证阅读,才有可能去除这种感性认知的极端表现。”[88]他要求学生们想象自己是世界文学课程的教师,以此选择自己想收入这个课程的各种文本。在此之外,他也为学生们给出七种可能的类型,包括“杰出作品”、“经典作品”、举世闻名之作、全球流通的作品等。学生们对世界文学有不同看法,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经典性”与“永恒性”,从而也引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与大写的世界文学并非自证自明的概念,而它们却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自相矛盾的话语和教学理念的讨论对象。”[89]在这个课程上,学生们采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英国文学历史上的某些作品,更加强调作者所生活的时代里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与跨语言互动。[90]其他美国大学教师也给出了教授世界文学导论课程中的成功案例,他们采用的方式“具有反思性、对话性,并考察文本背景”[91],将学生放在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中,从而“在本土中找到全球”[92],将文学视为以主题式研究方法来解答一套普世问题的“进行中的全球文化对话”[93]。
为了拉近个人经验与一般知识之间的距离,视域转化极为重要。伽达默尔(Gadamer)运用“视域”(horizon)这个概念来阐释理解(comprehension)如何进行。所谓“视域”,也就是“视觉上的范围,其中包括从某个定点能够看到的一切事物”。在思维模式意义而言,视域可以被收窄或拓宽,而新的视域也可能被打开。[94]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一个立足点上,知识就会被“封闭视域”局限。但当我们四下走动,关于过去的视域就会有所变动,从这样的视域之中“形成了全体人类的生活,并以传统形式存在”。[95]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时间性(temporality)和理解力(understanding)紧密相连于“不同视域的融合”(a fusion of horizons)——“理解力总是这些独立存在的视域之间的融会”。[96]视域转化也可以被用于展示历史学中的空间变化,比如说苏轼著名诗作《题西林壁》中就描写到庐山与观者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97]在张隆溪看来,诗中的庐山意象比喻说明的是“历史学并非仅是记录,也与阐释有关,牵涉到的层面远比这个具体的庐山比喻要多,因为这还包含了历史学家的参与投入,因此也牵涉到视域和视野的局限性”[98]。因此,要构建一段世界文学的历史,需要我们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进入具体的不同时空,以实现视域转化与融会。以香港文学历史研究学者陈国球所主持的香港文学大系丛书编撰过程为例,陈国球提出,在构建香港文学历史的过程中,必须采用多元视野角度,整合语文学研究方法和本体论探究:
从“香港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了解“境外”的观点其实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因为“香港文学”根本不容许一个画地自限的论述,如果我们不希望把香港文学史写成“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者“风土志”的话。“流动”与“越界”是香港这个城市以至香港文学的重要特色,有必要从内在与外缘的诸种因素去观测其构成与意义。[99]
更进一步而言,星丛范式处理的是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存在于艺术作品和其目标读者的阅读期望之间的,认识论与伦理学视域之间的距离;意识如何拉近这一距离;以及每篇艺术作品可能具有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转换文学经典化意识的旧有与现有形式。”[100]为了建立重写新的文学历史的系统方式,使其成为“在接受性的读者、反思性的论者与不断创作的作者身上实现的,审美接受与生产的过程”,姚斯(Hans Robert Jauss)举出七种观点:其一,“文学作品必须被理解为对话的创建过程,语文学学术研究必须建基于持续的文本重阅过程,而非仅仅基于事实”;其二,建立文学参考框架结构的客观能力必须基于对某个文本的阐释性接受;其三,某篇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它对某批读者产生影响的性质与程度;其四,通过重构期望视域,语文学家们能够探究文学作品存在于遥远过去的原本意图;其五,美学理论也要求我们将个别文学作品置于其“文学系列”之中;其六,一段新的文学历史应该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构语言学分析模式基础上建立;其七,文学历史的任务不仅包括将文学作品置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也在于将其置于“一段特别的历史,它与一般历史有所关联”。[101]我有充分信心认为,星丛范式将有助于构建这种富有新意与动感的文学历史。
四 作为结语:在全球化时代星丛化世界文学
在以上几节中,我在世界文学研究的普遍范围内探讨了星丛范式,它所面对的三个主要挑战来自语文学、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视野。从本雅明对星丛概念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从阐释学的角度清晰阐明了一与多、普世与特一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所提议的星丛化世界文学模式通过三个关键元素而得以运作:第一,不同出发点(points of departure),预设了不同世界的多元维度;第二,视域转换(horizon change),在文学作品的流通和翻译过程中得以实现;第三,普世诗学(universal poetics),也就是超越时空限制,使得跨文化理解与沟通切实可行的共同主题与价值观念。
在论证了采用星丛范式研究世界文学历史的可能与优势之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无法被理解掌握的无边星际宇宙,而它的历史牵涉星体与其观测者之间的多元对话,那么我们为何还要构建这样一段历史呢?达姆罗什并没有就此问题提供答案,而是以另外一个问题来应对之:这样的一段历史所反对的是什么?他认为有两个重要反对目标,也就是“狭隘受限的国族主义,以及无边无息的全球主义(a narrowly bounded nationalism and a boundless,breathless globalism)”[102]。实际上,这两个目标紧密相连,是现代社会中互为支持的同一结构。最近一项对国族主义和全球化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表明,国族主义概念来自某段特定的欧洲历史时期(1870—1945),“国族性”(nationality)出现于19世纪,作为有效工具,在全球范围而非本地范围巩固国家统治。当前对于国族主义的研究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主权,而是转为20世纪出现的关注超越国境前线的泛国族主义(pan-nationalism),同时也关注在21世纪变得极为重要的三大进程:全球资本主义的转换性传播、民族—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持续性、美国军事霸权。作为文化解决方案,我们也许可以合并特一性和普世性的思维进路,从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对文化进行概念化理解。[103]
国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的是普世/特一悖论(universal/particular paradox)的社会政治层面。今时今日,我们正在面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殖民主义形式,这种新殖民主义对世界文学研究构成威胁。在2011年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达姆罗什与斯皮瓦克开展对话,指出“世界文学研究很容易与全球资本主义最差趋势成为共谋,文化失根、语言破产,并且成为思想上的同流合污”[104]。在这些考量之外,他还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这种新殖民主义形势之外有所进展……当教授世界文学实际上已经变为方法上幼稚,文化上失根,语言上被损,而理念上成疑的举措?”达姆罗什建议我们采取这样的解决方式:引入更多语言研究、更多合作学术研究与教学,还有“大量的多元主义”。[105]
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世界文学的单一化且权威化的整体,那么星丛范式则并不适用。这种范式更加适用于为苏源熙所预测的全球多元文学世界重绘地图:“一种世界文学的模型,为数之不尽的文学世界创造空间,这个模型具有相对论性质(relativistic),而非决定论性质(deterministic)。但这也会被构建为任何一种想象空间:换言之,由各种差异性、暗示性、规则和排他性所组成。”[106]与其将世界文学展现为封闭系统,或者将其描述为一个问题,不如将它视为舍恩(Donald Allan Schön)所说的“行动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在这种反思中,整个过程“对于实践者用以巧妙应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一性与价值冲突情况的‘艺术’尤为重要”[107]。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思性行动而创造世界文学历史,意在抵抗任何类型的文学偏狭主义,认识论的独特单一性,性质同一的身份认同,这些都是奥尔巴赫警告我们要避免的。[108]这种范式邀请我们“走出文化的封闭圈”[109],拥抱从个人独特体验与视域出发的诠释多元主义。由此,我认为这是对深受全球化趋势与国族主义威胁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良方解药。
总结而言,星丛范式为纪廉(Guillén)所设计的世界文学范式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后者“从某些国族文学而兴起——从而使在地与普世,一与多之间的对话得以成为可能”。[110]如果要宣扬世界文学概念,促进其发展,我愿意向更多同道推荐星丛范式,望能有助于构建从各自视域出发的全球规模文学历史。文学研究学者可以致力在世界文学的众星体系里寻找更多的星群。在文学教学上也可以从当地文学出发,以此作为从本土角度观察的世界文学起源。个体读者可以在其跨文化阅读过程中寻找相似性,作出反思性观察与重构。这是人文学科最终的发展目标——为人类发展需要服务,帮助每个人找到独特但并不排他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全新范式的提出与合理化都不能否定其他的思维模式。有鉴于此,我将引用莫莱蒂关于文学历史模式的新颖全面论著的最后一句话,为此文作结:
当然,关于这些各异模式的兼容性,还有很多尚待探究,这些模式之间也还能够建立解释性的从属结构。但在此刻,开拓全新的概念可能,要比从每个细节上论证之,显得更为重要。[111]
[1] 【作者简介】黄峪,女,法国里昂大学跨文化研究博士,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发展统筹主任,《棱镜: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英文学刊执行编辑。研究方向为中法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理论。
本文英文原稿标题为“Constellating World Literature”,最初发表于Neohelicon2013年第40期。中文版于本刊首次刊登,作者略有修改,由作者和马文康共同翻译而成。
[2] See J.W.Von Goethe,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Being Appreciations and Criticisms on Many Subjects,trans.J.Oxenford,Honolulu:World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2010,pp.173-175;R.Wellek,“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S.G.Nichols,ed.,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287-295;and R.Étiemble,“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 Weltliteratur?”,in R.E'tiemble,ed.,Essais de littérature(vraiment)générale,Paris:Gallimard,1975,pp.15-36.
[3] G.Steiner,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1 October,1994,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5-6.
[4] C.Guillé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C.Franze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37-45.
[5] C.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39-48.
[6] H.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1.
[7] H.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6.
[8] H.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23.英文原文中的斜体部分在中文译文中以加粗表示。
[9] H.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35-36.
[10] C.Prendergast,ed.,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London:Verso,2004.
[11] D.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2.
[12] D.Damrosch,“Toward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New Literature History,No.39,2008,pp.482-489.
[13] M.R.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New York:Continuum,2008,p.4.
[14] M.R.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New York:Continuum,2008,pp.58-59.
[15] M.R.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New York:Continuum,2008,p.4.
[16] 达姆罗什用三个独创的术语,也就是“超级经典”(hypercanon)、“反向经典”(countercanon)和“影子经典”(shadow canon)来描述经典化的动态过程。See D.Damrosch,“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Hypercanonical Age”,in H.Saussy,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p.43-53.
[17] M.R.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New York:Continuum,2008,pp.139-142.
[18] M.R.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New York:Continuum,2008,p.59.
[19] 此文中的“占星学”定义来自Campion的著作:“一个雨伞概念,涵盖了一整批理念、想法与实践,都认为天空上的不同模式类型与地面上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关联。”Campion进一步表明,astrology这个源自希腊语的名词在其他文化如印度、日本和古巴比伦文化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表达。See N.Campion,What do Astrologers Believe?,London:Granta Books,2006,p.3.
[20] T.Barton,Ancient Astrology,London:Routledge,1994,p.1.
[21] N.Campion,What do Astrologers Believe?,London:Granta Books,2006,p.5.
[22] N.Campion,What do Astrologers Believe?,London:Granta Books,2006,pp.12-16.
[23] 在我看来,“西方占星术”指的是从巴比伦、埃及和希腊传统中生成的占星术。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占星术士对于辨认星丛和设定不同星座符号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中国占星术士以五行元素来命名天上的二十八个星宿。
[24] J.V.Stewart,Astrology:What's Really in the Stars?,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6,pp.55-58.
[25] Karl Popper也将天文学与社会学在长期预测与宏观预测方面进行比较:“如果天文学能够预测日食月食,社会学又为何不能预测革命呢?”See K.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1961,pp.31-38.
[26] V.Woolf,The Common Reader:First Seri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84,pp.1-2.
[27] I.A.Richards,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Routledge,1995,p.1.
[28] C.Guillé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C.Franze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2-13.
[29] L.Zhang,Allegoresis: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3.
[30] 在德国学术系统中,获得博士学位者应当准备一份“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也就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文字,并用以打动读者”,which is“a full-scale text,ready for impression,and submitted to the appropriate faculty of a university for public examination and judgment”,See George Steiner,“Introduction”,in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8.
[31] 德文单词Trauerspiel 本意是哀悼戏剧,这个词用来表示现代的巴洛克悲剧,与古典悲剧(Tragödie)有所不同。See“Translator's note”,in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6.
[32]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p.48-49.
[33]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51.
[34]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56.
[35]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28.
[36]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p.34-35.
[37] 在康德哲学中,现象(phenomena)指的是构建我们经验的表象(appearances)。
[38] See Steiner,“Introduction”,in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23.
[39] See R.Bontekoe,Dimensions of the Hermeneutic circle,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5,pp.2-4.
[40]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47.
[41]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p.47-48.
[42]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48.
[43]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34.
[44]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p.60-78.
[45]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p.121-122.
[46]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45.
[47]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47.
[48] Steiner,“Introduction”,in W.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ans.John Osborne,London:Verso,2003,p.24.
[49] G.Gilloch,Walter Benjamin:Critical Constellations,Malden,MA:Polity Press,2002,pp.70-71.
[50] Étiemble,“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 Weltliteratur?”,in R.E'tiemble,ed.,Essais de littérature(vraiment)générale,Paris:Gallimard,1975,pp.15-34.
[51] D.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1.
[52] D.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7-298.
[53] D.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300.
[54] D.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300-301.
[55] P.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trans.M.B.DeBevoi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4.
[56] P.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New Left Review,2005,p.71.
[57] P.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New Left Review,2005,p.72.
[58] P.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New Left Review,2005,p.74.
[59] P.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New Left Review,2005.
[60] P.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New Left Review,2005,pp.71-90.
[61] S.Lawall,“The West and the Rest:Frames for World Literature”,in D.Damrosch,ed.,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18.
[62] F.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No.1,2000,pp.54-66.See also F.Moretti,“More Conjectures”,New Left Review,No.20,Mar.-Apr.,2003,pp.73-81.
[63] F.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London:Verso,2005.
[64] F.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No.1,2000,p.55.“Problem”一词在英文原文中为斜体,在中文译文中“问题”一词作加粗处理。
[65] F.Moretti,“More Conjectures”,New Left Review,No.20,Mar.-Apr.,2003,p.74.
[66] F.Moretti,“More Conjectures”,New Left Review,No.20,Mar.-Apr.,2003,p.81.这句引文在英文原文中为斜体,在中文译文中作加粗处理。
[67] F.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London:Verso,2005,pp.1-2.
[68] G.C.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73,87.
[69] D.Damrosch,“Toward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New Literature History,No.39,2008,p.489.
[70] D.Damrosch,“Toward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New Literature History,No.39,2008,pp.481-495.
[71] E.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Maire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1969,p.7.
[72] E.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Maire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1969,p.10.
[73] C.Guillé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C.Franze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40.
[74] H.Saussy,“The Dimensionality of World Literature”,Neohelicon,No.38,2011,p.289.在英文原文中,“platitude”一词采用斜体表示强调,在中文译文里加粗表示。
[75] J.D.Pizer,“The Emergence of Weltliteratur:Goethe and the Romantic School”,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38.
[76] E.Apter,“Literary World Systems”,in D.Damrosch,ed.,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p.44-45.
[77] L.Zhang,“The Poetics of World Literature”,in T.D'haen,D.Damrosch and D.Kadir,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12,p.357.
[78] J.D.Pizer,“The Emergence of Weltliteratur:Goethe and the Romantic School”,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8-46.
[79] L.Zhang,“The Poetics of World Literature”,in T.D'haen,D.Damrosch and D.Kadir,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12,p.357.
[80] J.D.Pizer,“The Emergence of Weltliteratur:Goethe and the Romantic School”,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8-46.
[81] E.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Maire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1969,p.14.
[82] 周作人:《旧梦》,载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7页。
[83] 廖炳惠:《台湾文学中的四种现代性:以〈背海的人〉下集为例》,载廖炳惠《台湾与世界文学的汇流》,台湾:联合文学2006年版,第50—72页。
[84] L.Zhang,“The Poetics of World Literature”,in T.D'haen,D.Damrosch and D.Kadir,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12,p.357.
[85]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4页。
[86]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4页。此段引文原文为繁体,在此保留繁体原貌。
[87] 派泽用大写的World Literature名称来指代教学计划,而用“Weltliteratur”一词来指称歌德和其他学者所宣扬的世界文学概念。见J.D.Pizer,“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7。
[88] J.D.Pizer,“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8-149.
[89] J.D.Pizer,“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2-144.
[90] J.D.Pizer,“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in J.D.Pizer,ed.,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45-146.
[91] G.Harrison,“Conversation in Context:A Dialogic Approach to 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in D.Damrosch,ed.,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206.
[92] M.E.Rhine and J.Gillespie,“Finding the Global in the Local:Exploration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Teaching”,in D.Damrosch,ed.,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p.258-265.
[93] C.Ayers,“The Adventures of the Artists in World Literature:A One-semester Thematic Approach”,in D.Damrosch,ed.,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p.299-305.
[94] 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Continuum,2010,p.300.
[95] 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Continuum,2010,p.303.
[96] 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Continuum,2010,p.305.英文原文中斜体强调部分在中文译文中用加粗体现。
[97] L.Zhang,“The True Face of Mount Lu: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pectives and Paradigms”,History and Theory,No.49,February,2010,p.58.
[98] L.Zhang,“The True Face of Mount Lu: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spectives and Paradigms”,History and Theory,No.49,February,2010,p.69.
[99] 陈国球:《台湾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五期。
[100] H.White,“Literary History:The Point of it All”,New Literary History,Vol.2,No.1,1970,p.179.
[101] H.R.Jauss and Benzinger Elizabeth,“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New Literary History,Vol.2,No.1,1970,pp.7-37.
[102] D.Damrosch,“Toward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New Literature History,No.39,2008,p.490.
[103] D.Halikiopoulou and S.Vasilopoulou,“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Conflicting or Complementary?”,in D.Halikiopoulou and S.Vasilopoulou,eds.,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Conflicting or Complementary?,London:Routledge,2011,pp.186-199.
[104] G.Spivak and D.Damrosch,“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 discuss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8,No.4,2011,p.456.
[105] G.Spivak and D.Damrosch,“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 discuss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8,No.4,2011,pp.461-463.
[106] H.Saussy,“The Dimensionality of World Literature”,Neohelicon,No.38,2011,p.293.
[107] D.A.Schön,“From Technical Rationality to Reflection-in-action”,in D.A.Schön,ed.,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Aldershot,Hants:Avebury,1991,p.50.
[108] E.Auerbach,“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Maire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1969,pp.1-17.
[109] L.Zhang,“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Theory,Politics,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Modern China,Vol.19,No.1,1993.
[110] C.Guillé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C.Franze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33-34.
[111] F.Moretti,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London:Verso,2005,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