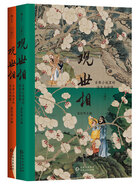
二
清议与清谈的话术转换
在中国古代,可能很少有一部小说会像《世说新语》一样,与哲学、宗教、思想和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今天的读者如果想了解汉魏六朝的思想文化史,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啃”那些思想家的著作,不妨先读读《世说新语》。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士大夫、学者、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在看似“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语狂欢中,我们与他们相识、相交、对话,于是乎,一个生动而又鲜活的思想世界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打开了。
清议与清谈
要说从学术、思想和文化的角度给《世说新语》“定性”,我还是更认同陈寅恪的“清谈全集”说: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6]
这段话不仅揭示了《世说新语》与魏晋清谈的关系,还特别指出,魏晋兴盛起来的清谈,在汉代就已“原起”(“起自汉末之清谈”
);而此书之所以要以汉末政治家陈仲举、李元礼诸人开篇,是为了“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余英时则从士文化的角度立论,认为“《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尤大于其下限也”。[7]两人不约而同,都提到《世说新语》“时代之上限”,虽然没有明说,其实已经暗示了作为魏晋清谈源头的汉末清议。
关于汉末清议的产生背景,《后汉书·党锢列传》的一段话最可参考: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汉末清议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昏聩的一种激烈的批评。其内容主要有二:一是政治批评,所谓“裁量执政”;二是人物臧否,也即“品核公卿”。前者,有太学生与士大夫圈子的游谈和互相标榜可以为证;后者,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汝南的“月旦评”。《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这里的“核论”,也即“深刻切实的议论”,和前面的“处士横议”“危言深论”,都是汉末清议在言说方式上的重要表现。因为清议表达了对当时政治的批判,自然引起宦官集团和皇帝的不满,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元年(168),清议名士先后遭到两次“党锢之祸”的清洗和弹压,陈仲举、李元礼等人相继罹难,天下士子,噤若寒蝉。于是,清议不得不转为清谈。
从清议到清谈
“清谈”一词,汉末已见,最初与“清议”可以互称,其中也有人物批评的内涵;到了魏晋,才更多地指向“抽象玄理之讨论”。在《世说新语》中,清谈又有“谈玄”“玄谈”“清言”“玄言”“口谈”“剧谈”“微言”“言咏”等多种异称,因为清谈主要盛行于魏晋,故而常称作“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根据唐翼明在《魏晋清谈》一书中的定义,可知:“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8]
相比清议,清谈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纯学术”的倾向,似乎与政治无关,不过,揆诸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就曾指出:
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
陈先生说清谈“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后汉书·郭泰传》记载:“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这里,“危言核论”再次出现,与“危言深论”正相映照,但前面却多了“不为”两字。这说明,颇有预见力的郭林宗已经敏感地嗅到了清议运动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故而不得不严格遵循孔子“邦无道,危行言孙”的教诲,将言论的方式、尺度控制在合乎时宜的范围内,以求规避不该有的安全隐患。他的“不为危言核论”,应该可以视为“清谈”的前奏和序曲。再看《世说新语·德行》第十五条:
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9]
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一向以佯狂放达著称,为什么司马昭会说他“至慎”呢?无他,盖因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与曹魏集团政争严酷,“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
)。政治高压之下,有识之士不得不明哲保身,以求全身远祸。阮籍的“言皆玄远”,比郭泰的“不为危言核论”更进一步:郭泰是尽量不说于己不利的话,阮籍则是说归说,却说得云遮雾障,玄虚缥缈;而“未尝臧否人物”,也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这分明是把“清议”的核心要素彻底删除了。我们把两则材料一对比,就可知陈寅恪所言不虚。
所以,一方面须承认,清议和清谈本质上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无论清议还是清谈,无不与现实政治有关,两者既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又有一种逻辑上的因果联系,甚至在清议鼎盛的时代,已经有了清谈的萌芽和端倪。
从“危言核论”到“言皆玄远”,印证了在言说方式上汉末清议向魏晋清谈的转变,而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异所形成的内在“张力”,在郭林宗和阮嗣宗的“话术”转换中得到了缓解和弥合。可见,清谈表面上似乎不牵扯政治,但在根本上却和清议一样,都是严酷的现实政治“应激反应”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