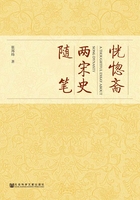
关于宋代避讳[1]
——研习钱大昕著作的一个读书报告
论及避讳学,即刻想到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追根溯源,不应忘记乾嘉巨子钱大昕(1728~1804)。陈垣甚至将钱氏盛赞为“清朝唯一的史学家”[2],认为:“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应推钱竹汀(大昕)先生。他对于避讳学虽未著成专书,然却有极精密的研究”。其名著《史讳举例》便是为纪念钱氏200周年诞辰而作。陈垣说:“我对于此题所用的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3]仅就宋代避讳而论,钱大昕的考论就很有分量。温故知新,而今仍可从中获得若干有益的认知与启迪。鉴于钱氏有关论述散见于多种著作,本文先择要分类摘录如下,并稍作评介,最后略抒个人感悟。
一 地名避讳
要言不烦是钱大昕论事行文的一大特色。其《十驾斋养新录》卷11《避讳改郡县名》条宋代部分云:“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为梅州、石镜县曰石照。父名宏殷,改宏农县曰常农(本曰恒农,史家避真宗讳改)、殷城县曰商城、溵水县曰商水。太祖名匡胤,改匡城县曰鹤邱、胤山县曰平蜀。太宗名光义,改义阳军曰信阳、义武军曰定武、昭义军曰昭德、崇义军曰崇信、保义军曰保平、感义军曰感德、彰义军曰彰化、南义州曰南仪、孝义县曰中阳、义川县曰宜川、义兴县曰宜兴、义章县曰宜章、郴义县曰桂阳、通义县曰眉山、方义县曰小溪、义宾县曰宜宾、义宁县曰信安、全义县曰兴安、信义县曰信宜、义伦县曰宜伦、义清县曰中庐、归义县曰归信、丰义县曰彭阳、招义县曰招信、正义县曰蒙山、富义监曰富顺。仁宗名祯,改祯州曰惠州、永贞县曰永昌、浈阳县曰真阳、浈昌县曰保昌。神宗名顼,改旭川县曰荣德。孝宗名眘,改慎县曰梁县。理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避圣祖讳,改元武县曰中江、朗州曰鼎州、朗山县曰确山、朗池县曰营山。天圣元年,避章献后父讳,改淮南之通州为崇州、蜀之通州为达州、通利军曰安利、通化县曰金川。大观四年,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曰西和州。廿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曰期思。”[4]这段文字看似冗长,实则简洁,其信息量之大、涉及面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涉及今四川省即多达10例,眉山、宜宾、富顺、中江、营山、达州六地分别因避宋讳由通义、义宾、富义、元武、朗池、通州而改今名。“(改)胤山县曰平蜀”,在今旺苍县境内;“(改)方义县曰小溪”,即今遂宁市船山区;“改旭川县曰荣德”,即今荣县;“(改)通化县曰金川”,在今理县东北。涉及今河南省之处也不少,恕不一一列举。
文中论及宋人避金朝讳,钱氏仅举二例。此种现象值得重视,或可作为宋金互称南北朝、相互承认的例证。陈垣《史讳举例》将其拓展为“宋辽金夏互避讳”,列举五例。如“《金史·章宗纪》:‘明昌四年,遣完颜匡使宋,权更名弼,以避宋讳。’”[5]尚有可补充者,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金史·海陵子光英传》记载,与改光州为蒋州同时,改“光化军为通化军”[6]。宋辽金夏互避讳原因何在,钱、陈二氏未做任何说明。其实“互避讳”并非常态,仅出现于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出使、绍兴和议之后等,系应景或应急之举。《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载:光州“绍兴末改蒋州,寻复旧”[7];《宋史·地理志四》载:光山“避讳改期思,寻复故”[8];《方舆胜览》载:“通化军复为光化军。”[9]
千虑一失,文中可商之处有二。一是通州改名达州,钱氏本人另有一说:“今考李氏《长编》亦载于乾德三年,殆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当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为“蜀之通州”非因避讳,系“避重名”,早在宋初已改名。二是宋代军有两种,不容混淆。钱氏曾多次强调,其《廿二史考异》卷69《宋史三》云:“宋时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如北海军后升潍州是也。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10]文中所举七军,仅义阳即信阳军系“小郡之称”,义武、昭义、崇义、保义、感义、彰义六军乃“节度军号”,似不应以“州郡名”相称。
地名避讳不限于郡县名,山名之类也在避讳之列。《廿二史考异》中有两例:其一,改“恒山”为“镇山”。《宋史·礼志》:“秦将王翦镇山伯。”钱氏案曰:“当是‘恒山’,避(宋真宗)讳,易‘恒’为‘镇’。”其二,改“桓山”为“魋山”。《宋史·王巩传》:“登魋山,吹笛饮酒。”钱氏案曰:“‘魋山’本‘桓山’,史家避(宋钦宗)讳改。”[11]桓山,在徐州境内,之所以改为“魋山”,或与山上有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之墓有关[12]。《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十二》作“栢山”[13],当属另一种避讳方式。
二 姓名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下《避讳改姓》条称:“陶谷本姓唐,诗人彦谦之孙,避石晋讳(后晋高祖石敬瑭),改陶氏。汤悦本姓殷,名崇义,初仕南唐,入宋避讳,改今姓名[14]。金履祥先世姓刘,避吴越讳,为金氏。”[15]陶谷、金履祥因避五代十国讳而改姓,殷悦则是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名讳而改姓汤。敬姓者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改姓恭。《宋史·艺文志七》:“《恭翔集》十卷。”钱氏案曰:“即敬翔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殷姓除改姓汤,改姓商者为数更多。《宋史·艺文志三》:“《目录类》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钱氏案曰:“本姓殷,避讳追改。《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商文圭《从军稿》”,“《五行类》有商绍《太史堪舆历》,皆本‘殷’字也”。钱氏指出:“殷璠《丹阳集》一卷,见《总集类》。而《别集类》又有商璠《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改‘殷’为‘商’,其实一书也。”[16]修史者不知姓氏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原因之一。
《十驾斋养新录》卷7《沈尤同族》,其依据是费衮《梁谿漫录》卷3《氏族》:“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17]名列“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便是例证[18]。陈垣《史讳举例》补充了一些姓氏避讳的例证,如文彦博本姓敬,更姓文[19]之类。但质疑“沈尤同族”:“尤姓由来远矣。”[20]有学者也认为此说不确,其主要理由是沈字去水旁,不是尤字[21]。
关于名讳避讳,《廿二史考异》卷75以杨承信改名杨信为例:“杨承信,《通鉴》作杨信,盖避汉隐帝(刘承祐)讳,去上一字也。”[22]同书卷73所举例证较多,如:王晦叔“本名曙,避英宗讳,称其字”;程正柔“本名匡柔,避讳改”;龚颐正“本名惇颐,避讳更名”;蔡元道“本名惇,避讳称其字”;朱景玄“宋人避讳,易为‘真’字,如玄武为真武也”;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亦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许恭宗“即许敬宗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钱氏指出:《宋史·艺文志》“《别集类》前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或改为‘光’,或改为‘正’,其实一书也”;“《艺术类》有张仲商《射训》”,商“本‘殷字’”。[23]
至于如何改名,办法不尽相同。《廿二史考异》卷70以宋初名将刘光义避太宗讳为例,指出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行”,改名廷让;二是缺笔,书“义”“为‘乂’”;三是以近音字替换,改“义”“为‘毅’”[24]。于是刘光义一人以四种名字出现于不同史书。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称:刘光义,“《宋通鉴长编》作‘刘光义’;《蜀梼杌》作‘刘光乂’;《宋史》作‘刘廷让’;《东都事略》作‘刘光毅’”[25]。
《十驾斋养新录》卷16《文人避家讳》称:“古人重家讳。”并以司马光及眉山苏氏为例。司马光“父讳池,每与韩持国(维)书,改‘持’为‘秉’,取其义相近”。其实“礼不讳嫌”,“不避无妨”。苏序之子苏洵,著文“改‘序’为‘引’”。其孙苏轼“不为人作序,或改用‘叙’字”[26]。《潜研堂集·文集》卷29《跋剡录》指出,此书的作者高似孙“为文虎之子”,“书中屡称(其父为)先公翰林”,并“称袁虎为袁彪,亦是避其家讳也”[27]。
三 官职避讳
因避讳而改官职名称较常见,其时间则长短不同。历时短者,如改通判为同判之类,前后不过十年而已。《廿二史考异》卷69引《嘉泰会稽志》:“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如改通进司为承进司,……诸州通判为同判,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之类是也。仁宗亲政皆复故。”[28]历时长者,如部署改称总管、签署改称签书,从宋英宗即位到南宋都如此。至于北宋前期,系追改。《宋史·高化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钱氏《诸史拾遗》卷4案曰:“宋初,武臣领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曰副都部署,曰部署。英宗即位,始避讳,改部署为总管。史于仁宗朝诸臣,如此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降滑州总管,改真定路副都总管;……皆依后来避讳之称。”[29]《宋史·职官志二》:“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廿二史考异》卷71案曰:“太平兴国四年,置签署枢密院事,以枢密直学士石熙载为之。八年,以张齐贤、王沔同签署院事。景德三年,马知节、韩崇训亦为签署。史家避英宗讳,改署为书尔。治平中,郭逵以检校太尉同签书枢密院事。签书之名始于此。”[30]《宋史·宰辅表一》:“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石熙载自枢密直学士迁签书枢密院事。”《廿二史考异》卷74案曰:“‘签书’当作‘签署’。张齐贤、王沔、杨守一、张逊、冯拯、陈尧叟、韩崇训、马知节、曹玮、王德用诸人皆除签署或同签署。史家避讳,追改为‘书’字。”[31]
任职不仅限于避圣讳,而且要避家讳,《唐律疏义》有明文规定。《十驾斋养新录》卷6《居官避家讳》条:“《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32]这一禁令为《宋刑统》卷10《职制律·冒荣居官》所沿袭[33],宋太宗雍熙二年诏令、宋仁宗嘉祐六年诏令[34]及《庆元条法事类》[35]等法律文书在原则上予以重申。避讳办法有二:一是更改出任官职,如由任著作佐郎改任秘书丞。林岊因其父祖名著,不能担任著作佐郎。《潜研堂集·文集》卷28《跋九朝编年备要》:林岊“开禧三年三月,除秘书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讳,改除秘书丞。……见《中兴馆阁续录》”[36]。二是更改职官名称,如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宋史·宰辅表一》:“建隆元年二月吴廷祚自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廿二史考异》卷74案曰:“《本纪》作‘同中书门下二品’。廷祚父名璋,故改平章事为二品。后晋天福四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故也。《(宰辅)表》书平章事,误。”[37]慕容延钊又是一例,“以(其)父讳章,当为使相,不带平章事,并拜同中书门下二品”[38]。但此法“仅止一再见,几于特创”,限于优礼“开国勋臣”[39]。
从广义上说,官员谥法可归属职官制度。钱大昕对有宋一代的谥号曾潜心研究,下过大功夫[40]。依钱氏之见,改“贞”为“正”是官员谥号避讳的典型例证。《潜研堂集·文集》卷30《跋挥麈后录》称:“宋初,李昉、王旦皆谥文贞。后来避仁宗嫌名,改为‘正’字。范希文、司马君实之‘文正’即‘文贞’也。谥法有‘贞’无‘正’,宋人避讳有‘正’无‘贞’,二名不当并用。”由于对此茫然无知,以致产生两大错误。一是不懂唐代谥法,改“贞”为“正”。有学者以为唐代谥法已有“文贞”,其主要依据是“(王溥)《唐会要·谥法篇》‘贞’俱作‘正’”。钱氏强调:“此后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当回避‘贞’字。”二是“正”“贞”并用,甚至认为“正”优于“贞”。“元时谥耶律楚材、许衡文正,而马祖常、曹伯启别谥文贞。此当时太常不学之失,而后遂沿用之。”[41]对于钱氏此说,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6《谥文正》有申论,可参看[42]。
四 文书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卷7《宋人避轩辕字》条称:“予见宋板经籍遇‘轩辕’二字辄缺笔,初未详其说。后读李氏《通鉴长编》”,方知宋真宗尊轩辕黄帝为远祖、赵玄朗为圣祖,于大中祥符五年诏:“圣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内外文字不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乃悟‘轩辕’二字阙笔之由”[43]。于是孔子谥号由“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宋代诸如此类的文字禁忌不少,特别是宋徽宗时期。《十驾斋养新录》卷7有《孔子讳》《避老子名字》《僧道不称寺观主》《政和禁圣天等字命名》《禁人名寓意僭窃》等条。据《能改斋漫录》《容斋续笔》记载:“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当时还不许人们取名“大明”“丕显”“孙权”“刘项”等。政和八年,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昔皇祐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睹。”另一则是:“政和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钱氏引用《至正直记》:“‘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以‘丘’字朱笔圈之。凡有‘丘’字,读若‘区’,至如诗以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44]
书名避讳是文字避讳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宋史·艺文志》著录颜师古一人著有两种书,一种叫《刊谬正俗》,另一种叫《纠谬正俗》。《廿二史考异》卷73指出:“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已见《经解类》,而《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此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其实一书也”[45]。又如《艺文志》“前有刘时靖《时镜新书》五卷,后有刘靖《时鉴杂书》一卷,宋人避讳,改‘镜’为‘鉴’,其实一书也”[46]。修史者不知书名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又一个原因。
因禁忌森严,宋人行文遣词、印行书籍,均极审慎,“于宋讳皆阙笔,即‘慎’‘敦’‘廓’‘筠’(等同音近音)诸字亦然”。避讳如若还有正面意义,其作用或在于方便后人解决版本疑难。钱氏《跋宋太宗实录》称:“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47]《十驾斋养新录》卷1《朱子四书注避宋讳》列举钱氏所读版本沿袭宋本避宋讳之处,如改齐桓公为“齐威公”,“避钦宗讳”;“‘慎’字,避孝宗讳,以‘谨’代之”;“一正天下,改‘匡’为‘正’,避太祖讳也”;“‘逊者,礼之实也’,改‘让’为‘逊’,避濮安懿王(允让)讳”;“‘正子’,改‘贞’为‘正’,避仁宗讳也”[48]。
五 两点感悟
研读钱大昕有关宋代避讳的论述后有些点滴感悟,下面妄言一二。
其一,关于宋代避讳,略有所知易,弄个清楚难。既往研究虽有若干[49],只怕仍有深究的余地。某些基础性的问题未必就明白。如避讳在宋代究竟是习俗还是制度?其遵行或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对此,钱大昕、陈垣两大家无专门讨论,今人多以习俗相称,也有称为制度者。愚意以为,从总体上说,宋代避讳兼具习俗与制度双重性质。避讳以其避讳对象而论,大致可分为帝王圣贤讳与为家族尊长讳两大类[50]。后者简称“家讳”,其性质大抵属于习俗,但前文所述任职避家讳,就不只是习俗,系载入法律的制度性规定。避家讳习俗的流传程度因社会层级与文化水平而异,这一习俗在文盲居多的下层社会很难广为流传,而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上层社会则很盛行,因而钱大昕有“文人避家讳”一语。前者简称“圣讳”,其性质不仅是弹性较大的习俗,更是刚性较强的制度,如若违犯,将受惩处。《贡举条式》等书所载《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等法规中均有避讳条文[51]。可见事涉官方文书和科举试卷,这些法规显然执行得尤其严格。应当指出的是,即便避圣讳,也具有一定的弹性。首先法规本身就不一致,有二名不偏讳者,如宋太宗赵光义最初的规定是:“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52]也有二名偏讳者,如“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53]。但实际上“‘玄’字不避者多”[54]。上举李焘《长编》“上曰玄”,钱大昕引用时改为“上曰元”,系避清圣祖玄烨讳。可见推行时多有变通。又如按规定当“改‘殷’之字为‘商’”[55],其实改为汤者也有之。有的规定过期作废,改通判为同判之类是其显例。又如“避老子名字”之禁“未久而即弛矣”[56]。有的规定反复变更,宋太宗的避讳方式便多次调整。开宝九年十月的规定是不避“光”字,只避“义”字及其嫌名,“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议郎为宣奉郎。”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宋太宗降旨:“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换言之,即“光”“义”二字均不避讳。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宋真宗下诏:“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57]严令“光”“义”二字均必须一概回避。如此前后折腾,或可作为我国传统时代的所谓法制随意性较大的又一小小例证。
其二,关于钱大昕本人,有学者在积极评价其卓越成就之余,感叹其“文字过于简略”。[58]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在下则更偏向于赞赏钱氏论事行文简洁、直白、明快,不兜圈子弯弯绕,无闲言冗语,认为这一学术风格在当今尤其难能可贵。前辈学者往往如此告诫后学:不要研究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无法求证的问题、没有多大意思的问题;不能大而无当,空话连篇,也不能钻牛角尖,鸡零狗碎;不应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邓广铭开导其弟子:“《辽史》上说得很明白,乣,军也。乣,就是军,没那么复杂。”[59]无独有偶,钱大昕也曾与其友人简而言之:“乣亦部落之称。”[60]“乣”究竟是什么,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评,但对钱、邓两大家不把问题复杂化的主张,高举双手赞成。程应镠教诲其高足:写文章“要干净简炼,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61]。我同样高度认同,当长则长,能短更好。以此为标准,反躬自省。我那本《婚姻与社会·宋代》或许还算较为简洁,至于《宋代皇亲与政治》,不一定是“王大娘的裹脚”,但分明是注了水的。“米不够,水来凑。”这种现象在当今印行的学术论著中似乎并不少见。其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字海之中,叫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难以把握其主旨要义。让我们学学钱大昕,少说些废话,多挤些水分吧。离题远了,搁笔。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1] 本文为2017年9、10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钱大昕与宋史研究”读书会而作,感谢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2] 与陈垣相似,陈寅恪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中,称赞钱大昕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页)。
[3] 陈垣:《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讳学》,《史讳举例》附录,中华书局,2012,第237~238页。
[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杨勇军整理,上海书店,2011,第220页。
[5] 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12,第43~44页。
[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五月辛未,中华书局,1988,第2968页;脱脱等:《金史》卷82《海陵子光英传》,中华书局,1975,第1853页。
[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8《舆地考四》,中华书局,1986,第2498页。
[8] 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第2184页。
[9] 祝穆等:《方舆胜览》卷33《光化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第598~599页。
[1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9《宋史三》,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75页。
[1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0《宋史四》、卷77《宋史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84、1077页。
[12] 苏轼:“有言郡东北荆山下,可以沟畎积水,因与吴正字、王户曹同往视,以地多乱石,不果。还,游圣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无棺椁,或云宋司马桓魋墓。二子有诗,次其韵二首”(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3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768~770页)。
[1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5《经籍考七十二》,中华书局,1986,第1936页。
[14] 南唐司空汤悦“即殷崇义,池州人也,姓犯宣祖讳,故改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79,第40页)。
[1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下《避讳改姓》,上海书店,2011,第428页。
[1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2、1018、1026页。
[1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7页。
[18] 《无锡县志》卷3上:“宋尤袤,字延之,其先闽人,本姓沈。因避王审知讳,去水姓尤,来居无锡。至袤,遂为无锡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1:“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髙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茍氏”(中华书局,1983,第167页)。
[20] 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12,第18页。
[21] 程羽黑:《十驾斋养新录笺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263~264页。
[2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57页。
[2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18~1032页。
[2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57页。
[25]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3,第732页。
[2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334页。
[27] 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20页。
[2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81页。
[29]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录《诸史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548~1549页。
[3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4页。
[3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4页。
[3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29页。
[33] 窦仪等:《宋刑统》,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65页。
[34] 岳珂:《愧郯录》卷10《李文简奏稿》,朗润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129~133页。
[35]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77页。此事承蒙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双怡博士告知。
[36]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99页。
[37]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4页。
[38] 岳珂:《愧郯录》卷10《同二品》,中华书局,2016,第133页。
[39] 岳珂:《愧郯录》卷10《改易职事官名称》,中华书局,2016,第127页。
[40] 钱大昕称:“宋时后妃、诸王、文武臣僚得谥者,熙宁以前,载于宋次道(敏求)《春明退朝录》;庆元以前,载于王明清《挥麈后录》,然亦不无遗漏。予尝合宋、王两家类次而增补之,宁宗以后,则据正史,参以它书,补缀其阙,较之王圻《谥法考》所得盖已多矣”(《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41页)。
[41]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41页。
[42] 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6《谥文正》,清光绪会稽章氏刻本。
[4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39页。
[4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3~144页。
[4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18页。
[4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20页。
[47]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98页。
[48]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46~47页。
[49] 据我所知,最早断代专文探究这一历史现象的是朱瑞熙《宋代的避讳习俗》一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一文有重要补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硕士生周源在吴晓萍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宋代避讳制度研究》一文认为宋代已形成礼法合一的避讳制度(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忠礼《略论历史上的避讳》一文则是宋史研究者通论历代避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2篇第6章“避讳改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8~645页。
[50] 民间忌讳与行业避讳,本文不涉及,可参见向熹《汉语避讳研究》第10章“俗讳”,商务印书馆,2016,第379~421页。
[51] 丁度等:《集韵》附《贡举条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313~315页。丁度是北宋人,书中所载南宋文献系后人增添。参见朱瑞熙《宋朝〈贡举条式〉研究》,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73~291页。
[52]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8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壬申,中华书局,1979,第1802页。
[54]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8页。
[55]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3页。
[5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3页。
[57]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8页。
[58] 王瑞明:《钱大昕考订〈宋史〉的卓越成绩》,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第284页。
[59] 杨若薇:《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发言》(2017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
[60]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616页。
[61] 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