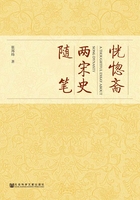
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1]
——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一 引言:过犹不及
对于宋代社会,学界有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远的结论性认识。
一种是“平民化”。邓小南认为,平民化是从唐到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个“度”。邓小南颇有防范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被无限引申的担心,她在访谈中格外强调:“所谓‘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2]本人对此深表赞同。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3]一文,虽然仅着眼于狭义的文化,但多少包含这层意思。文中的某些认识,或可作为宋代平民化趋势的例证。当年之所以想到这个论题,是受到当代史学大家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启示。他在书中将宋代“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4]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件事之一。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未把《导论》一书读懂,至少领会不深。
另一种是“平民社会”。有学者将宋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5],只怕就失度、过度了。其主要依据是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所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或系‘贵族’之误)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岂止平民社会而已,并且是“纯粹的”。这段文字,20世纪80年代我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曾部分加以引用。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其唐宋变革论,对“平民社会”一说虽心存疑义,但并未深究,仅在注释中有所表达[7]。
钱穆“贵有‘系统’”“本诸‘事实’”[8]的治学主张,重在“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变动”[9]的治学方法,受到学者广泛认同。其学问素有博大精深之称,其论著新意迭出,无论对错,均极具启发性与刺激性。由于钱穆名望很高,宋代“平民社会”论当前在学界较为流行。“平民社会”到底何所指?钱穆究竟是如何阐述的?近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学习钱穆有关论著(以下简称“钱著”),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于是写下这篇读书报告,其中难免有尚未读懂与妄加评议之处,尚祈同好指教。还要说明的是,钱穆阐述论题总是瞻前顾后,本文虽以宋代为题,不得不上挂下联,或有离题较远之嫌。
二 钱穆的原意是什么
我也曾下意识地以为,钱穆将宋代社会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多读了些钱著之后才发现,此说并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
第一,钱穆并非仅有平民社会一说。众所周知,他是位学术“常青树”,其学术生命极长。宋代是个什么社会?在不同时期,或因视角有异,或因语境有别,钱穆有多种说法。除平民社会而外,还有“平等社会”(第177页)、“平铺社会”(第171页)、“白衣社会”、“科举社会”、“进士社会”、“士人社会”、“四民社会”[10]等。其中含义相同或相近者较多,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平民社会和四民社会。钱穆论及四民社会、士人社会之处,甚至多于平民社会。
第二,在钱穆看来,平民社会早已产生于“秦以下”,宋代不是“第一个”。他关于平民社会的阐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平民社会从秦、汉开始,并非始于宋代。他在许多情况下将秦以下的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历史大单元。钱穆说:“秦、汉以下的中国”,“当时已无特殊的贵族阶级的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第105页)。又说:秦、汉时代“平等社会开始成立”(第177页)。还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第245页)。二是时至宋代,平民社会更纯粹。钱穆说:“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11]又说:“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之存在了。”(第190页)还说:“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12],“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1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三 “平等社会”与“士人社会”
何谓平民社会,据我阅读所及,钱穆始终未曾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众多论述中,不难发现,所谓平民社会是指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全国人民参政”(第242页),“一律平等对待”[14]。其关键之处在于“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15],“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因此他又将平民社会称为“平铺社会”。所谓“平铺”即无高低上下之分,社会各色人等一律平等,都是平头百姓;“散漫”即“无组织,不凝固”,以致“没有力量,无可凭借”,犹如“一盘散沙”。在钱穆的辞典里,平民社会、平铺社会、平等社会是同义词。他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16]
如果说平民社会一词较费解,那么平等社会一语则相当直白。平民社会论是对还是错?弄清其含义之后,答案应当是明确的。“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吗?秦汉以后果真再也没有特殊势力了么?赞同者想必寥寥。行文至此,或可搁笔。下面要稍加补充的是,在钱著中反证比比皆是。
钱穆的“四民社会”说与其“平民社会”论便自相抵牾。他在力主平民社会论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17]如前所引,所谓平民社会是平铺的,无组织,无等差。按照钱穆的解释,四民社会则有高下,有领导,有中心。他说:四民社会“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如东汉社会便是“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第126页),并称:“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18]钱穆反复强调:“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19];四民社会“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20];“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21]。因此,他又将四民社会称为“士人社会”。依我之见,士人社会说较之平民社会论有可取之处。既无强大经济实力,又处于无权地位的平民绝无主持与领导社会的可能,“平民社会”论很难成立。
问题在于:普通士人就能主导社会吗?按照钱穆的论说,士人是“一个中间阶级(或可改作‘阶层’)”[22],介于贵族与平民两者之间。其下层依然是标准的平民,而其上层则近乎贵族。俗话说:“书生不带长[23],说话都不响。”真正有可能主导社会的不是普通士人,而是钱穆所说的“书生贵族”[24],即人们常说的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解释者甚多,如费孝通、陶晋生[25]等。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结合,主要是指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正如钱穆所论,士人即使出身平民,一旦出任高官,即在社会上“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其“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容易在少数家庭中占到优势”。他将此种情形称为“变相的世袭”(第127~128页)。由此可见,“士人社会”之说仍然不妥。如果将士人社会改称士大夫社会或书生贵族社会,其说服力也许会增强许多。
四 两大特殊势力
钱穆的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其主要依据是:“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26]尤其是“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第162页)。仅以西周式封建贵族而论,这一论断大体属实。但断言秦以下即是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只怕并非“语语有本,事事着实”[27]之论了。人们即刻会想到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和明清时代的绅士。其实,这两大特权阶层或称特殊势力均见于钱著。
对于门阀士族,钱穆曾反复阐述,可谓深中肯綮。他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第128页)。又说:“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28]还说:“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29]钱穆将他们称为“变相的世袭”、“变相的贵族”(第128页)、“门第新贵族”、“封建贵族特权势力”(第176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说:他们“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第128页)。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又说:“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他们将学问与书本作为“变相的资本”,由“读书家庭”变为“做官家庭”。钱穆指出:门阀士族“无异于一传袭的封建贵族”,是一种“书生贵族”[30]。如果按照钱穆的言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唐代门第势力正盛”[31],门阀士族前后延续岂止七八百年而已,而是长达近千年。这一特权阶层经久难衰正是秦以下无特殊势力一说的绝好反证。
对于明清时代的绅士,钱穆虽然涉及较少,但对“地方自治”、“地方绅士”乃至“土豪劣绅”均有所论述。钱穆所谓“地方自治”,包括经济方面的义庄、义塾、学田、社仓等,营卫方面的保甲、团练等以及乡规民约。他说:“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说全由新儒家精神为之唱导和主持。”精神可以倡导,怎能主持?他接着又说:“宋后的社仓,则由地方绅士自己处理”(第191页)。这下明白了,地方自治的主持者少不了地方绅士,他们或与地方政府共治地方。地方绅士为地方上做了些有益的事。但作为特殊势力,他们“长者”与“豪横”这两种类型或两种面相均兼而有之[32]。其豪横者“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钱穆出于义愤,斥之为“土豪劣绅”[33]。所谓绅士,即曾做官或将做官的读书人。他们可称为继门阀士族之后的又一种“书生贵族”。正如相关研究者所说:“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34]明清时代乃至近代的绅士同先前的门阀士族一样,都是平民社会论的反证。
五 两个“无定型时期”
剩下的问题是:西汉与宋代无特殊势力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提出两概念”说起。其一是“有定型时期”,“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如西周至春秋的封建贵族。以此为标准,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长期获得特殊地位,可视为继西周、春秋之后的又一个有定型时期。其二是“无定型时期”,这一时期从战国延续至汉代(主要是指西汉),“旧的特殊势力(指封建贵族)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指门阀士族)尚未形成”。这个历史阶段,“在社会上并无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到东汉,“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而唐代则是第二个无定型时期,“旧的特权势力(指门阀士族),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当指绅士),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35]。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说:唐代“可称为门第过渡时期”[36]。过渡时期的含义与无定型时期大体相同。第二个无定型时期延续到宋代,作为两大特殊势力之一的绅士尚未固化。
按照钱穆本人的论述,处于第一个无定型时期的西汉,并非没有特殊势力。西汉初期的诸侯王,即是一例。在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之后,汉高祖又裂土封王。钱穆认为:此举“较之秦始皇时代,不得不说是一种逆退”(第100页)。除诸侯王外,还有“无异于往昔之封君贵族”[37]的商贾与任侠。钱穆指出:“‘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期社会上的两种特殊势力,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变相的新贵族’”(第118页)。这批靠经营盐铁发家的富商大贾被当时人称为“素封”[38],其含义为虽无封邑,但富比封君。与此前的封建贵族和此后的门阀士族不同的是,诸侯王、商贾、任侠这三种特殊势力延续时间不长,尚未固化为阶层,在汉景帝、武帝时即先后被清除。可是汉武帝之后,又有郎吏。所谓郎吏,是指太学生入仕为官,补郎补吏者。钱穆认为,此项制度乃士族之温床,由此“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39]。南朝人沈约所说“汉代本无士庶之别”[40],是身处门阀时代之人倒看历史,专指门阀士族尚未成型,而不能作为西汉无特殊势力的佐证。
处于第二个无定型时期的宋代,其情形与西汉相似。钱穆对宋代的特殊势力论述不多,但学界的探讨颇多。当时的特殊势力,既有势官地主,又有士大夫阶层。“势官地主”这一概念由白寿彝提出,他解释道:“势,当时叫作形势户。官,当时叫作官户。势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的。”[41]对于官户、形势户,研究最深入、最详尽的是王曾瑜,请参看其《宋朝阶级结构》[42]一书及《宋朝的官户》、《宋朝的形势户》等文[43]。对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既有研究难以备举。可稍加补充者有三:一是钱穆本人就指出,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崇高”,“为社会之中坚”[44]。面对这一现实,当时有人将宋代社会直呼为“官人世界”[45],换言之,即士大夫社会。杂剧说得更形象:“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46]二是熙宁四年枢密使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47]吴晗早于20世纪40年代便在《论皇权》一文中引用,并在《论士大夫》一文中列举了士大夫享有的种种特权[48]。三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有明清时代绅士的雏形。如辞官闲居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的南宋执政何澹[49]与退休回到家乡华亭县(即今上海嘉定区华亭镇)的明代首辅徐阶就相仿佛,两人虽然面相不尽相同,但在地方上的地位与作为很相似。或许可以如是说:绅士阶层肇端于南宋,成型于明代。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西汉与宋代都处于无定型时期,其平民化趋势较为明显,只怕是个不争的事实。钱穆将西汉政府称为“平民政府”、西汉政治称为“平民政治”,言过其实。但他所说的“大臣出自民间”(第110页),“乡村学者尽有被举希望”(第125页),平民学者讲学之风很盛,太学生“不限资格,均可应选”(第103页)等,都是平民化趋向的表征。至于宋代,钱穆的论述不限于所谓平民参政,也不限于平民学者“讲学风气愈播愈盛”,讲学内容“牵涉到政治问题”(第190页),等等。其重点在于文化,并使用了“平民化”这个概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从“文学平民化的趋势”说起,直到“平民的美术”(第197页)、平民的音乐、平民的工艺,并称:“唐代的美术与工艺,尚多带富贵气”,“否则还不免粗气”。“一到宋代才完全纯净化了,而又同时精致化了”。“民间工艺实在是唐不如宋”(第201页)。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中又讲到书法特别是绘画的平民化及其与理学精神的关联[50]。宋代的平民化趋势涵盖面广,无论是从充实、细化还是梳理、深化的角度,都还有文章可做。
六 结语:权力社会
世上万事万物均处于变换不居之中,动态是绝对的,静态是相对的。钱穆治史重在“明变”,并将变化分为“大变”与“小变”[51]的主张,本人举双手高度赞同。就中国古代特殊势力演变史而论,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实现万世一系、永不倾覆的幻想。确如钱穆所言,总是旧的特殊势力在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在形成。这是大变。从小变来说,正如钱穆所说:特别是“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显贵家庭,不过三四代,家境便是中落了”(第248页)。然而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特殊势力和特权家庭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不曾缺席。大而言之,贵族之后,士族继起;士族之后,绅士继起。尽管其权势有大小之别,从总体上看“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趋势,贵族非士族可比,而士族又非绅士可比。翦伯赞当年曾强调:“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52]对于贵族、士族、绅士应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殊势力始终存在,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学界有权力社会一说。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称为权力社会,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并不确当。但与平等社会一类的说法相比,权力社会一说似乎较为合理,关键在于它揭示了包括宋代在内的秦汉以下社会的不平等性。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极具不平等性,于是出现了《不平歌》这类激愤之词:“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53]不平等社会在古代历史上周而复始,翻来覆去。人们回望往古,才不免有“六道轮回,出路何在”之叹。平等在中国古代只是美妙的向往。当时人曾述说:“此间不问人贵贱,不问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间正不正尔。”[54]“此间”者,虚拟世界阴间也。不平等是我们的祖先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社会现实。一言以蔽之,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一说只怕是想当然耳,恕我直言不讳。
[成荫、陈鹤两位学友曾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原载《历史教学》2017年(下半月刊)第8期]
[1] 本文由2017年9月30日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两份讲稿综合整理而成,感谢河大宋史中心、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2] 郑诗亮、孟繁之:《邓小南谈对宋史的再认识》,《东方早报》2016年12月16日。
[3] 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367~400页。
[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第175页。钱氏此书有关“平民社会”的论述较多。以下凡引此书,均仅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
[5] 张宏杰:《第一个平民社会》,《新京报》2013年1月4日。
[6] 钱穆:《理学与艺术》,《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280页。《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7]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84页。
[8] 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2页。
[9]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6页。
[10]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5~48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769页。
[1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669页。
[13]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4、26页。
[1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32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117页。
[1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71~175页。
[17]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7页。
[18]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849页。
[19]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8页。
[20]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561页。
[21]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52~53页。
[22]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9页。
[23] 原话是“参谋不带长”,恕我妄改。
[2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5页。
[25] 参见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第9页;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1,第2~10页。
[26]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399页。
[27] 钱穆:《国史新论·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页。
[28]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7页。
[29]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561页。
[3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4~35页。
[3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86页。
[32] 可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474~536页。
[33]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699页。
[3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页。
[35]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3~16、21页。
[3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7页。钱穆既称“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又说唐代“可称为门第过渡时期”。唐人郑仁表有诗云:“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王定保:《唐摭言》卷12,中华书局,1959,第136页)。唐代既“尚官”又“尚姓”,“正盛”说与“过渡”说相比,“过渡”说较妥。这类前后差异明显的说法在钱著中不止于此。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前面刚说:“政权普遍公开”(第171页),后面就说:“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第173页)。又如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一书中,前文称:官员“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第127~128页),后文又称:宋代官员的弟侄儿孙只能“自己寻觅出路,自己挣扎地位,他们丝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获得的光辉”(第161页)。果真如此吗?人们立即会想到宋代的恩荫制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有“宋恩荫之滥”一条:“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并有略带夸张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一语(中华书局,1963,第486~487、485页)。
[37]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59页。
[38]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3272页。
[39]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0页。
[40] 郑樵:《通志二十略·选举略二·杂议论上》,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1287页。
[41] 白寿彝:《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
[42]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2010。
[43] 王曾瑜:《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第197~446页。
[44]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492页。
[45] 洪迈:《夷坚志》支庚卷5《辰州监押》,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1177页。
[4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4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5370页。
[48]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第41、68页。
[49] 参见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50] 钱穆:《理学与艺术》,《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279~812页。
[51]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6页)。
[52]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
[5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扶箕诗》,中华书局,1980,第343页。
[54] 《夷坚志》乙志卷5《司命真君》,中华书局,1981,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