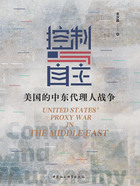
第二节 代理人战争的内生特性
代理人战争的运作场景和方式比较特殊,涉及施动方与代理人在一种非对称的代理关系中互动。在这种环境中内生了一些代理人战争的特性,如信息非对称、相互制约、非正式、非正当和代理人自主性等,而这些特性又折射出代理人战争的复杂面貌和不确定性。
一 非对称性:代理人优势
在代理人战争中,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权力、实力和身份的非对称性,这一点是公认的常识,毋庸赘言。但是强大的施动方也有其脆弱之处,而代理人尽管要弱小得多,却依然拥有弱者所特有的非对称优势。在几乎所有的代理关系中,无论是正当或非正当的,代理人都至少拥有信息和能力两个方面的非对称优势。实际上,为优先满足和扩大私利,代理人有足够的动机将非对称优势转化为与施动方进行博弈的杠杆。
(一)信息不对称优势
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占据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优势。艾瑞克·雷霆格尔(Eric Rittinger)指出:“代理关系涉及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条件下签订的正式或非正式合同。委托人将一些权力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则负责代表委托人工作。”[51]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指出:“信息非对称指的是一些行为体掌握其他行为体所不知的私人信息。”[52]在代理人战争情景中,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代理人对如何执行代理议程和实际付出的努力程度有深入的理解,而这些不容易被施动方所衡量或观察。
信息不对称为代理人谋求私利提供了掩护,使其具备了“进退自如”的主动权,而它的存在使得行为体之间进行诚实的合作变得异常困难。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海伦·米尔纳都指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确定性是阻碍协议达成与合作低效重要根源之一,一些行为体可能比其他行为体对一种形势所占有的信息要更多,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因此有能力和政治优势操纵一种关系或者成功地实行欺诈行为。[53]由于国家在相对能力和意图上存在错误展示(故意夸大或示弱、欺诈、掩饰等)的动机,因此对私人信息的需求非常强烈。理性行为体都试图占有相对更多的信息,因为“信息就是力量,信息会有利于那些掌握私人信息的行为体”。[54]信息非对称通常导致施动方面临代理关系管理难题,“尽管委托人当然希望代理人完全像委托人一样履行其职责,但是鉴于两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代理人更了解自己的偏好、自己的表现以及手头的任务”。[55]信息不对称可能会鼓励代理人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偏离施动方的指示,且仍然获得代理关系带来的好处。[56]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会发生。在经济学、风险管理和保险行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常被用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情形下代理人懈怠的原因:代理人操纵私人信息以推进不利于委托者的利益,所以委托—代理关系总是在追求一个“次优”结果。[57]
“逆向选择”是描述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准确和不同的信息,信息较多的一方更有优势,前者能够利用这种信息优势(隐藏的信息)来使自己受益。代理人具有委托人所不了解的专业知识,当代理人利用这种优势来追求与委托人不一致的目标,或隐藏动机时,逆向选择就发生了。在代理人战争中,选择可靠的、有能力的代理人对于推进施动方的利益至关重要。[58]然而,信息不对称使得施动方遭受“逆向选择”风险:如何选择最优代理人?在代理关系建立前,施动方缺乏对等的知识和信息,对潜在代理人的能力、可靠性、信誉等“过往记录”(track records)了解甚少,只能经过大致的筛选、评估,并从中找到那些貌似具有相似利益的代理人。但是,这就有可能导致选择错误。相对施动方而言,代理人更了解自身的行为和意图,一些无能或不忠诚的代理人就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来隐瞒自身真实能力、可靠性和动机,通过欺骗来获取施动方更优惠的授权和资助条件,进而获得更大的收益。以上这些例子都是不受欢迎的代理人懈怠行为。“逆向选择”主要是指代理人利用“隐藏信息”(hidden information),如隐藏资质、能力和动机信息等,对此,委托人又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识别。简而言之,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欺骗施动方,导致施动方无法识别和选择一个可靠的代理人。
道德风险是指参与合约两方(A和B)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A所面临B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B在达成交易后改变其行为(隐藏的行为)而不必因此承担任何代价,反而将风险转移到A。[59]道德风险在保险市场时有发生。例如,在没有健康保险时,有些人可能由于费用太高或生病不严重而放弃医药治疗。但是在健康保险变得可利用后,有些人可能要求保险提供方支付没必要发生的医药治疗费用。又如,在购买火险后,有些人可能会较少关注防火措施,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简言之,一旦获得施动方的授权、承诺和援助后,代理人就像获得了“保险”,且完全明白自身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代价主要由施动方来承担。
在代理人战争中,道德风险无处不在,例如代理人倾向于懈怠和偏离,包括:不投入全部的努力、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谋求持续的援助,甚至采取与施动方的偏好和指示相反的行动,等等。肖恩·麦克法特将代理人战争中的道德风险比喻为租车行为,人们随意驾驶租来的车,而不像爱惜自己的车那样,这会鼓励司机的破坏行为,代理人类似“用完即弃”的“被租借的力量”(rented force),他们不必为承担后果而小心行事。[60]实际上,当代理人“事先”(ex ante)获得施动方的援助和可信的安全担保后,更加明白自己的重要价值以及施动方的“兜底”角色,道德风险就可能发生。“有了来自强大施动方的保险,代理人更有理由选择暴力而不是妥协,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多的资源来挑起一场冲突,给自己和施动方带来风险”。[61]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可能将施动方卷入持久的冲突中。例如,如果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俄罗斯将失去其在中东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大马士革完全明白自身对俄罗斯的重要价值,因而相信克里姆林宫提供“保险”协议是可靠的,敢于采取激进方式来打击反对派武装,并预料到俄罗斯会动用安理会否决权来阻挠国际惩罚行动。[62]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代理人拥有同时制造“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机会,一旦其认为这样做可以谋取更多的私利,就会导致施动方遭到欺骗和承担不想要的后果。
(二)能力非对称优势
一方面,地方代理人具有本地专长(local expertise)优势。作为施动方的国家与非国家的地方代理人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及“主从”关系结构,但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务实合作,因为二者各自的非对称优势可以创造利益互补空间。外部施动方需要从地方代理人那里“取长补短”,获得大量高质量、大规模的当地知识,降低“事必躬亲”的昂贵成本和代价。一般而言,不同的个人、团体和公司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这使得他们从事一项活动比一个团体做所有事情更有效率。[63]地方代理人更了解当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当地居民偏好、人口结构、地形地貌、关键基础设施等信息,同时高度熟悉当地事务和社会网络,因而能在地方更有效地执行某项任务,有能力去做施动方不能或不便做的事情。
在如何借助地方代理人的相对优势问题上,美国有丰富的经验。例如,“基地”组织残余于2001年12月逃到普什图族控制的阿富汗托拉博拉山区(“基地”组织前首领本·拉登被怀疑藏匿在此)。美国国防部原本准备授权大规模部队进入追击,但其常规地面部队并不熟悉那里的语言、文化和地形,若直接插入普什图核心地带,则可能造成大量伤亡,并破坏情报部门尝试与当地人建立合作的努力。最终,中情局和特种作战部队招募了一支对那片土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地方代理人部队即“普什图联军”(美国称其为“东方联盟”),以更隐秘、安全的方式介入其中。[64]又如,在叙利亚战场上,美国也需要依赖库尔德等反对派武装提供空袭所需的地面位置信息,为提高后者的情报能力,美国还向其提供无线电、GPS等设备和相关培训。[65]此外,有些学者也主张国家常规军增进对战争场地本土知识的了解。肖恩·麦克法特认为,获得本土化专长应该成为美军发展新能力的重要一环。他建议美国军事外交官应沉浸在一个地区,多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和政治,并观察当地人如何打仗和为什么打仗,进而提升根据美国利益影响地方事务的能力。[66]
另一方面,代理人具备“干脏活”的能力与优势。对于施动方而言,一些“见不得光”又必须做的任务常使得它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亲自干“脏活”要冒着巨大的道德、政治、法律代价和遭到报复、冲突升级的风险。那么,一种替代方案是施动方希望代理人去发挥“脏手”角色,因为“代理人(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漠视战争的传统规则,代之以非常规手段,而国家行为体则受限较多,这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突破现代战争的规范限制,其战略和战术选择也比国家行为体更加多元和丰富”。[67]而且,外界似乎比较容易接受代理人固有的道德瑕疵,其充当“脏手”角色符合人们心理和经验上的某种预设,以至于它从事违背国际规范的罪恶活动时也不会引起广泛的“诧异”。与此同时,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对其进行责任和证据追溯、认定存在诸多难题。“非正规代理部队与施动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常常掩盖了命令的发布方式以及交战规则的实际制定者。当一名代理战斗人员在冲突国家的宪法秩序之外行动,为空袭提供目标坐标,提供化学武器袭击的情报,或动员网络机器放大虚假信息时,往往跨越红线而不会产生任何后果”。[68]代理人的“脏手”能力不但不构成代理关系形成的主要障碍,而且成为可资利用的“优势”。例如,当美军需要利用安巴尔部落酋长来打击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时候,后者曲折的过去和可疑的忠诚都可以被忽略,麦克法兰甚至认为:“一个好人不可能成为酋长,这些人是无情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69]又如在冷战之初,面对美国拥有核威慑能力这一事实,苏联自身不太可能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但可能的策略是把卫星国作为其干“脏活”的代理人。[70]
二 相互制约性:“被抛弃”与“被牵连”
在代理人战争中,“被抛弃”与“被牵连”是常见现象。由于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实力差距和身份差异,其利益关切点存在明显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敏感度不一样,即施动方一般更担心被牵连,而代理人则更担心被抛弃。由于双方都知道彼此更担心哪一种后果,这一点可以被用来制约彼此。
“被牵连”主要是指代理人接受施动方的援助后,其行为变得更加激进、冒险,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人权规范和基本道德,施动方因代理人的出格行为卷入不想要的事件中,并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代理关系中的被牵连,如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对联盟的描述:“各国既面临寻求维持盟友支持,同时又将避免被其盟友拖入不必要的战争的风险。”[71]对施动方而言,自身的安全和声誉都可能被代理人牵连。例如,美国通过支持越南共和国政府遏制苏联扩张,鼓动了越南共和国政府的冒险,导致灾难性的冲突升级和美军大规模直接卷入。当代理人采取冒险的行动导致冲突失控或敌人的报复,施动方可通过明确否认、沉默、降低资助代理人的力度等方式切割彼此间的关联。例如,2021年10月,美国指责伊朗支持其民兵武装攻击美军的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伊朗对此矢口否认。当代理人的暴力行为严重挑战人道主义和国际规范时,施动方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牵连,同样会撇清自身的责任,增加证据回溯的难度。例如,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一直指责由莫斯科控制的雇佣兵公司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深度参与了非洲马里、中非等国家的广泛武装冲突,折磨和杀害数以百计的平民。对此,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表示,有关俄罗斯雇佣军参与屠杀的说法是“肮脏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72]
“被抛弃”是指施动方不再满意代理人的表现,或代理人的利用价值降低、丧失,或施动方可以选择其他代理人,那么继续支持代理人不再符合施动方的利益和预期,代理人就可能被施动方抛弃。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当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离,且戈尔巴乔夫对西方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阿富汗抵抗“圣战”组织(Mujahedin)在代理人冲突中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并很快被美国所抛弃。[73]又如,1961年,美国中情局扶植的古巴流亡势力试图武装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然而,在赫鲁晓夫的恫吓下,美国总统肯尼迪拒绝为古巴流亡武装的登陆提供空中掩护,以至于中情局策划、主导的“猪湾行动”完败,而古巴流亡组织领导人也对美国的抛弃进行了绝望的抨击。[74]
“被牵连”和“被抛弃”是一组相互制约机制。在联盟中,强国害怕被牵连,弱国担心被抛弃,但二者实际上也构成相互制约(mutual binding/constraining)的机制,对被牵连和被抛弃的恐惧会因盟友不同的实力、意图状况而存在差异,实力对比、意图匹配程度这两个变量正是通过影响成员国对“被牵连”和“被抛弃”的恐惧来制约其管理联盟意愿。[75]在代理人战争中,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实力、身份、意图严重不对称是加剧施动方对“被牵连”和代理人对“被抛弃”的恐惧的根本原因,双方都有可能利用对方的“恐惧点”来实现互相制约。
在施动方一边,它可以通过改变(或威胁改变)对代理人的支持力度、更换代理人乃至中断(或威胁中断)代理关系等负面激励的方式来触碰代理人的“恐惧点”(即“被抛弃”),“一方越强大,弱小一方脱离联盟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强国对弱盟友的控制力就越强”。[76]因而,施动方可以通过抛弃(或威胁抛弃)代理人来迫使后者遵从代理议程。
在代理人一边,它也可能采取不恰当的行为(包括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残暴的手段、超出授权之外的偏离、懈怠等)或公开暴露代理关系的运作方式来逼近施动方的“恐惧点”(即“被牵连”),使后者付出一系列高昂的观众成本:国内外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而面临国内政治掣肘、公众反对和国际社会谴责。与此同时,施动方还可能因为代理人的冒险行为卷入“不想要”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中,并因此增大遭到敌人报复的风险。一方对代理人的支持往往招致对手以同样的方式反制,这种“连锁反应”使有限的冲突升级为全面冲突,并可能造成更大的不稳定。[77]
在有些情况下,“被牵连”与“被抛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现象。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支持南非在安哥拉开展代理人战争的证据被报道后,美国官方开始后退并否认此事。然而,南非国防部长揭露:“我们是在美国人的赞同和了解下越过边界的,但他们却让我们陷入困境。”[78]在这个例子中,南非被美国抛弃,而美国同时也被南非牵连。
可以说,代理关系中始终存在“互相牵连”(mutual entanglement)的风险:一方面,施动方与当地代理人并肩作战,可能纵容后者的冒险和出格行为,从而反噬自身的声誉;另一方面,当地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关系过近,也可能被视为入侵者的“帮凶”,从而导致自身合法性遭到严重削弱。
三 非正式与非正当性:“影子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施动方和代理人不希望它们的互动被公开,以及其行为受到正式契约和道义上的约束,更希望代理人战争中是以非正式和非正当的“便利”方式运作,这为彼此的互动提供了足够的灵活度。如果不能获得这种灵活度,那么代理人战争的运作也将变得异常困难。
首先,代理人战争通常以非正式、非正当的方式和逻辑来运作,绕开了道义和法理的约束。在战争中,不择手段地获胜与道德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迈克尔·沃尔泽称之为“战争中的两难困境”。[79]为约束、规范武力的使用,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克劳塞威茨、格劳秀斯、约翰·罗尔斯等先哲努力构建起战争的界限和“正义战争论”的道德标准、悠久传统:正当的理由和正确的意图,合适的权威和公开宣战,最后的诉诸手段,较高的成功可能性,武力与威胁相称,不得轻蔑人类的生命,避免伤害非战斗的平民。[80]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为了绕开对武力使用所施加的法理和道义束缚,一些国家转而将“蒙面力量”(masked force)引入战争中,以非正式、非正当的方式继续滥用武力。在代理人战争中,“冲突中的重要角色很可能是准国家组织,它们不会按照《日内瓦公约》这样的国际法律规范行事。危险在于战争变得无法无天和难以预测,因为代理人武装组织将不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目前都接受的多边协议的约束”[81]“与遵循着基本国际规则的国家行为体相比,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伦理相对较为薄弱,往往无视既有国际规则”。[82]代理关系通常是施动方秘密地支持“处于武装冲突国宪法秩序之外的第三方常规或非正规”的武装代理人去应对具体的、显著的威胁的一种非正式、非正当安排,在这种安排中,很少会出现清晰、严谨的书面权责、承诺约束条款,它们很难被直接观察到。[83]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非作歹的成本、难度和受关注度比主权国家低得多,由它们承接国家行为体想干而不便干的非正当勾当就显得“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国家资助恐怖主义组织开展非正当的(illicit)代理人战争。一旦国家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参战,就打破了常规战争的规范和框架。
其次,由于代理人战争的非正式、非正当性,它对于那些不愿直接使用自身力量的国家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在代理人战争中,施动方与代理人都力图通过秘密和模糊行动来保留合理推诿,以便为未来的行动创造灵活度和战略优势。而非正式、非正当的安排使国家能够挑战对手,同时获得“合理推诿”的便利性。[84]此外,由于代理关系被隐形化处理,这进一步强化了“影子战争”的吸引力。当国家支持代理人战争与自身标榜的正义、合法形象相抵触,代理关系就以“去证据化”方式运作,在“授权-控制”环节上尽量满足无文本化、模糊性、隐蔽性和弱关联等要求。例如,“代理人战争中的‘脏手’(dirty hands)问题也许是美国最关心的,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从自身榜样的力量和军事力量中获取合法性的国家来说,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85]因此,施动方希望代理关系被隐形化处理,避免其声誉受到牵连。实际上,不透明的运作成为责任追溯障碍以及施动方决策者从事非正当活动的“遮羞布”,且代理人的“脏手”角色会受到纵容和保护。
总之,代理人战争以非正式、非正当的方式运作,极大地便利了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去道义化”互动,这不但导致“蒙面力量”被引入广泛的冲突,也增加了“影子战争”对任何想发动战争而不承担后果的人的吸引力。[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