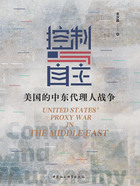
一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代理人战争(Proxy Warfare)通常被概念化为战略,其中一方鼓励或利用另一方为了自己的战略目的而进行战争”。[9]它被广为接受的逻辑所主导:施动方在干涉目标国事务的过程中可以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代理人,从而避免自身卷入与对手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历史中确实存在大量可以印证代理人战争“魅力”的案例,以至于在人们当中形成一种刻板的认识:施动方发动代理人战争是一种成本小而收益大的政策选项,代理人将遵照施动方的利益和偏好行事,是可以被操纵、被牺牲的完美工具。
然而,上述认识与一些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不符。实际上,代理人战争中经常出现“双刃剑”(double-edged sword)、“逆火”(back fire)、“倒吹”(blow back)等“适得其反”的现象。公元前11世纪前后,古代中国部落之间的征伐与合纵连横十分频繁,小邦西周成为大邑商的代理人,替商讨伐戎狄部落。据史料记载,周屡次帮商击败戎狄,商王文丁感动之余封季历(周部落领袖)为“牧师”(“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牧师”。参见《古本竹书纪年·殷纪》)。而周一方面对商保持形式上的臣服,为商征战,以换取商的信任与庇护;另一方面又以伐敌之名攻城略地,积蓄自身的力量。当商陷入与东夷的持久战而消耗过度之际(“纣伐东夷而陨其身”,参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周武王趁机伐纣,最终在牧野之战中灭商。[10]约公元前240年,迦太基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利用多国雇佣军与罗马军队作战,但雇佣军非但不愿意冒险,反而发生叛变,并调转矛头攻击迦太基人。[11]东汉末年(约公元2世纪),曹操拉拢西凉马腾、韩遂等军阀势力,并利用后者的骁勇善战击败了袁尚(袁绍之子)武装集团。自此,曹操、马超(马腾之子)相互猜忌,二者关系生变。公元211年,马超起兵叛变,与曹军交战并被击败。[12]
1914—1916年,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代理人战争介入墨西哥的内部冲突,先是扶持和利用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领导的武装团体颠覆了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军政权,但是卡兰萨在成立新政权问题上却拒绝美国的指使。这迫使威尔逊当局不得不更换代理人,转而扶持卡兰萨的前副手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而比利亚的军队失利后,又立即遭到抛弃,比利亚愤而枪杀美国人来报复威尔逊当局的背叛。[13]1940年初,希特勒入侵丹麦,试图在丹麦安插一个傀儡政府,做他所要求的一切。但是丹麦傀儡政府阳奉阴违,不断削弱德国的控制。布兰登·梅里尔(Brandon Merrell)从该历史事件中提出疑问:“为什么像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却无法从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代理人身上永久地提取出顺从的行为呢?”[14]
代理战争在冷战期间很普遍,美国和苏联在核恐怖的压力下转向通过代理人进行竞争,避免直接军事对抗。通过对冷战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尽管美苏为避免卷入直接冲突而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动代理人战争,但是不难发现“两霸”的代理人经常有效地“反向操纵”它们,导致普遍的“尾巴摇狗”(the tail wagging the dog)和“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现象频繁出现。[15]1960年代,美国试图在越南扶植一支代理部队,后者在获得美国的“保险”后更加冒进,逐渐将美国拖进这场注定要失败的冲突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阿富汗反苏战争(1979—1989年)中,美国所支持的“圣战”代理人在十年后成为最令人恐惧的反美恐怖主义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16]1980年代,印度甘地政府试图利用“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介入斯里兰卡内战,但后者反过来利用印度的庇护扩张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不仅导致印度失去对后者的控制,还反遭报复,1991年“泰米尔猛虎组织”暗杀了印度总理拉吉·甘地。历史表明,施动方在代理人战争中可能陷入“弄巧成拙”的尴尬境地。特别是施动方在强化代理人能力的同时,也可能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敌人。[17]
进入21世纪,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之后,代理人战争再度流行,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分析人士的关注。与目标国内部冲突有利害关系的外部国家寻求间接使用军事力量,以尽量减少政治、财政等成本以及生命代价,将战争外包给非国家行为体的趋势得以延续,正如中东、非洲和乌克兰等地区的广泛冲突所表明的那样。尽管代理人战争在所谓的“廉价”、风险转移、便利性等动因的驱动下而频发,但是代理人战争的进程和后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在中东发起的多场代理人战争基本走向“事与愿违”的境地。自2003年以来(截至2020年),美国利用代理人战争介入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的冲突,其基本模式大同小异,即通过美国特种部队、训练、武器转移、情报分享、空中援助等方式赋能目标国的当地代理人,试图利用后者帮助自己“火中取栗”。例如,2006年夏季美国为镇压“基地”组织的暴乱,大力资助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民兵开展“觉醒”(awakening)运动,并取得不错的成效。然而,逊尼派部落也反过来利用美国的支持,谋取了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此,布莱恩·威廉(Brian Glyn William)指出,逊尼派武装部落的忠诚难以被完全收买,其长期后果难以控制。[18]又如,2015年以来,美国为打击“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组织,试图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展为高效的代理人。尽管后者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表现出色,并赢得美国的赞赏,但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同样利用美国的支持,趁机招兵买马,不断开疆拓土,努力谋求更大的自治权。此外,代理人战争对法治建设和国家对冲突后环境中的暴力垄断构成长期挑战,如美国提供给代理人的武器很容易被转移到意想不到的接收者手中,这种转移会助长腐败的战争经济,从而有助于个别强人(包括部落、暴乱分子或意识形态领导人)利用战争来提高自身地位。[19]
上述事实说明代理人战争过程和结果是不确定的,它可能有利于施动方以低成本的方式达成目标。与此同时,具备高度自主性的代理人也会追求与施动方不一致的目标,所谓的“完美”代理人只存在于施动方的幻想中,实际上是罕见的。“代理人战争往往会在(代理人)做得太少和(施动方)代价太高之间达到政治上的‘最佳点位’(Sweet Spot)。尽管如此,在现实中,这是一种不完美的战争形式”。[20]代理人始终抱有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的动机,施动方并没有办法彻底消除代理人的自主性。那些自私自利、不忠不满的代理人甚至反过来操纵施动方,躲避施动方的管控,并可能阻碍、破坏、反噬施动方的利益。那么让人困惑的是:在代理人战争中,为什么施动方难以管控比自身弱小得多的代理人,而这背后的机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驾驭代理人战争又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