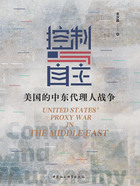
二 文献回顾
关于上文提出的问题,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一是关于代理人战争的理论讨论;二是关于中东爆发代理人战争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研究;三是关于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的实践和经验总结。这三类研究成果包含了代理人战争的一般性知识,也包括地区经验和具体案例的特殊性知识,它们共同构成了本书的初步知识体系,为解释美国为何难以摆脱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困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关于代理人战争的理论研究
在一般性理论探讨中,学界无法避开的两个紧密相扣的重要问题是:代理人的自主角色是否有意义?施动方能否及如何有效管控代理人?就前者而言,既有的研究形成两个基本范式:第一个是“施动方中心”范式,它侧重于施动方的利益和偏好,假定施动方可以单向度主导代理人战争的进程,而代理人在其中的能动性和自主利益被排除或者遭到严重低估、忽视;第二个是“代理人再发现”范式,它明显注意到代理人在代理人战争和代理关系中的非对称能动角色,并认识到代理人会谋求与施动方不一致的目标。整体来看,这两大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和关切点不同,似乎存在矛盾、对立之处。但是,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经历了互鉴、互纠的平衡过程,最终人们发现代理关系不是单向的主从关系,其固有的张力来源于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双向博弈。
1.“施动方中心”视角
在代理人战争研究方面,“施动方中心”视角是指学界过于高估施动方的主导能力,过度关切施动方的利益,忽视或贬低了代理人的角色。1964年,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界定代理人战争为“两个外部大国在第三国领土上发生的国际冲突,伪装成该国内部问题的冲突,并利用该国的一些人力、资源和领土作为手段,以实现占主导地位的外国目标和外国战略”[21]。在此界定中,代理人角色完全被“两个外部大国”所湮没,契合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逻辑。“在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被视为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工具,这导致理论片面集中在大国竞争上。在这一理论假设中,超级大国仿佛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朋友来对抗敌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只关注主要行为者的意图和代理联盟中的权力不对称,这样不但缺少代理联盟的生成机制,而且低估了内部冲突的动态、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22]
1984年,雅科夫·巴尔·西蒙托夫(Yaacov Bar Siman Tov)修正了代理人战争的概念,他认为代理人战争是一方应第三方的要求与另一方交战的战争。定义这样的战争的条件是应施动方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个要求,代理人就不会参战,即使它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有利益。[23]西蒙托夫虽然避开了“国家中心”范式,但是他几乎不给代理人的自主利益留有一丝空间。
安德鲁·芒福德(Andrew Mumford)则认为代理人战争是施动方与选定的代理人之间关系的产物。施动方是现存冲突动态之外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而选定的代理人是武器、培训和资金的接收方。简而言之,代理人战争是各国寻求推进自身战略目标,同时避免卷入直接、代价高昂和血腥战争的合理替代品,即施动方倾向于“通过将动力活动外包给第三方代理人来避免任何直接干预的方式”。[24]很显然,芒福德认为代理人只是施动方的战略中第三方“牺牲品”,也没有赋予其更多角色含义。
此外,“霸权决定论”的观点更加不会重视代理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在核威慑的压力下,美苏转而通过控制代理人来间接达成战略和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愿意冒直接介入冲突的风险。苏联解体后代理人之间的内战才逐渐结束,是因为外部支持者失去了兴趣并停止支持它们。[25]这种侧重两极结构的叙事忽视了被庇护者对冷战的动态过程和关键事件所起到的作用。总之,在代理人战争中,施动方被描述为一个利益、指令的输出中心,代理人则被视为“机械地”推进施动方所确立的目标和利益的“木偶”(puppet)。
既有研究一般基于施动方的“受益”视角,认为运用代理人战争可以获得战略利益并降低风险和成本,以至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称代理战争是“你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保险”。代理人战略主要是指无论在和平还是交战时期,施动方可以利用代理人来弱化、胁迫、破坏敌人的力量发展和进攻能力。[26]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和2010年发布的两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都将代理人战争作为一种“间接手段”(Indirect Approaches)或“混合战”(Hybrid War)的组成部分来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胁迫或威胁敌人。[27]同样,俄罗斯也被认为擅长利用代理人战略来建立冲突缓冲地带或冲突冻结区,以此控制和影响临近自己的苏联国家和地区。[28]施动方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具体“好处”主要包括:避免直接的正面冲突,减少自身的伤亡和漫长的资源投入;控制战争的规模和节奏,避免冲突升级;绕开国内的社会反战情绪、政治反对派、行政和司法程序的诸多限制,介入冲突的过程更加便捷、灵活;即使肮脏的代理人战争失败了,其给本土带来的损害和政治后果也较小,因为决策者还有否认、推诿(deniability)的余地;等等。简而言之,使用代理人战争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更便宜(cheaper)、更容易(easier)。[29]
最后特别指出的是,施动方主导范式过于重视施动方的利益和价值关切而忽视代理人自主角色,这是导致人们对代理人战争和代理成本理解不够充分的重要原因。
2.“再平衡”:“委托—代理”视角
既有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施动方中心”范式,代理人自主角色也受到关注。丹尼尔·拜曼(Danniel Byman)指出,代理人反噬施动方的自主行为应受到关注,“尽管(对施动方而言)有许多优势,代理人远非感激和顺从前者,也常常令施动方失望,当地代理团体经常走自己的路,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收受金钱和其他支持”。[30]与此同时,芒福德也关注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代理人也有自己的议程,尤其是代理人开始萌生自主念头以及向施动方伪造相异的战略目标解释,这使得冲突中的代理关系的管理必然是机警的。”[31]
代理人的自利和偏离行为对“施动方中心”范式构成了挑战。施动方“决定论”可能出于单方面的幻觉,并不符合实际。陈翔指出,在内战中代理人并非无自我利益或纯粹是为了施动方利益采取代理行动,代理人要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会积极借助施动方的力量力图改变内战国家的国内权力结构。[32]此外,施动方“受益论”也遭质疑,施动方纯粹是代理人战争的受益者吗?丹尼尔·拜曼对此泼了冷水:“代理人战争不仅仅是由代理人来承担战斗和死亡,对施动方也含有不可预见的后果。”[33]布莱恩·威廉姆斯(Brain Glyn Williams)通过对发生在伊拉克(2006—2008年)、阿富汗(1981—1998年)、波西尼亚(1992—1995年)和车臣(1999—2009年)的四场代理人战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代理人战争更像是“双刃剑”,施动方虽然可以迅速获得安全,但这种短期的胜利伴随着长期的代价,诸如冷战后阿富汗的动乱、波西尼亚的报复,以及车臣盗匪横行的环境。[34]
鉴于“施动方中心”范式无助于呈现代理人战争的复杂面貌,目前学界试图从委托—代理的理论视角来平衡它。
随着社会和产业的分工,“日益复杂之组织而演化的科层结构,则带来了限定委托—代理关系的正式结构”,[35]其中代理人因具备专业优势和特殊价值被委以重任来解决烦琐问题和“增效节支”。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科已大量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诸如公司治理(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互动)、政府治理(科层政府的分权与博弈、央地关系等)、国会监督(国会监督官僚机构)、国际组织运作(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授权)等正当代理情形,其中如何管控代理人则成为“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oery)(简称“代理理论”)的重要关切点。[36]达伦·霍金斯(Darren Hawkins)和韦德·雅各比(Wade Jacoby)指出,尽管代理理论的文献越来越复杂,但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委托人如何控制这些代理人,却对代理人试图规避这些控制的策略关注较少。因此,他们提醒学界,在研究“委托—代理”问题时,代理人的角色值得高度关注。[37]阿巴斯·法拉索(Abbas Farasoo)也持相同的看法:委托—代理理论都认为施动方向代理人行使不对称的权力是二者产生联系的基础,代理人在其主人的意志之外没有任何议程和自主权,这一理论使得代理人战争看起来是单方面的决策程序,忽略了代理人的角色和他们的偏好,在最坏的情况下,“被授权的代理人可能会变成其赞助者的掘墓人”。[38]
那么,研究代理人战争(非正当代理情形)时,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和基本逻辑是否仍然适用?事实证明,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向多种场景扩张,具备很好的理论渗透性和通约性,这为国际关系学界将其引入代理人战争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正式代理情形类似,代理人战争中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即在管控代理人谋求自主性问题上施动方面临一种权衡:虽然支持目标国的代理人往往比直接参与战争的成本更低,但冲突的授权也会带来一定的战略风险,尤其是施动方要担心的是代理人懈怠(agency slack)。因此,代理理论的基本逻辑和分析框架被引入代理人战争研究领域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国际关系学者运用代理理论呈现了代理人战争中的代理困境,包括代理关系中的固有张力,以及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双向博弈。在代理人战争中,代理人为何经常追求与施动方目标不一致的议程,这种差异背后的机理是什么?是否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约束代理人保持在设定的轨道?学界一直在推进、深化相关的讨论,目前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下。
第一,“成本—收益”权衡。泰隆·格罗(Tyrone L.Groh)指出,迄今为止,通过第三方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没有被充分考虑,代理人战争仍缺乏对成本和收益的系统性处理,代理人的自利特性和动机是至关重要的,会给冲突增加另一层复杂性。[39]故此,他从“成本—收益”视角对若干代理人战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山姆·海勒(Sam Heller)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发现代理人战争更像是追求“次优”结果的手段,例如美国在叙利亚进行的代理人战争并没有达成野心勃勃的“最优”目标,但支持“有问题”的反对派代理人继续战斗依然是一个“次优”的方案,至少可以增加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获胜难度、成本并保留美国影响叙利亚和中东事务的“杠杆”。[40]布兰登·梅里尔(Brandon Merrell)以“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德国占领丹麦(1940—1945年)期间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困境:缺乏足够的、可信的激励(奖励或惩罚)工具和代理人的努力成本(effort cost)不断上升。[41]
第二,“去中心化”的互动结构。冷战期间,当涉及代理人角色时,经常出现“尾巴摇狗”的比喻。霍普·哈里森(Hope Millard Harrison)认为有必要对过往冷战研究中的“超级大国中心”论进行修补,增加“卫星国”对冷战动态和关键事件的贡献。对此,他尝试以“去中心化”视角研究冷战期间苏联与民主德国关系(1953—1961年)。在他看来,苏东(德)关系比以前所理解的“更双边化”(more two-sided),民主德国不仅通过自己的政策限制了苏联的选择范围,也利用了美苏、中苏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紧张关系。[42]舍约·布朗(Seyom Brown)将“尾巴摇狗”作为“代理人战争陷阱”(Proxywar pitfalls)的一种形式,他指出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可能(也确实)被假定的代理人利用,因为后者不断地从超级大国那里勒索更多的援助。[43]
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博弈中,也存在大量的“尾巴摇狗”现象。艾弗莱姆·卡什(Efraim Karsh)对中东历史与政治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尾巴摇狗”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反对从全球强权政治支配的视角理解该地区事务,也不认同“中东人是缺乏内在自主动力的倒霉对象”的观点。[44]例如,坎迪斯·荣德(Candace Rondeaux)与大卫·斯特曼(David Sterman)指出,“‘法塔赫’‘巴解组织’‘塔利班’和‘北方联盟’之类的代理人并没有仅仅充当零和游戏中陷入困境的全球棋盘上的棋子,实际上巧妙地操纵了它们的施动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45]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中,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它的代理伙伴可以操纵上报给美国的情报,代理伙伴可以把当地的暴乱分子描绘成“基地”组织的一部分,也可以夸大受援部门的作战效力,其目的在于谋求美国增加整体援助规模和影响美国对这场斗争的看法。[46]
第三,互利的动机。安东尼·普法夫(C.Anthony Pfaff)明确指出:“施动方和代理人之所以进入这种关系,是因为这有助于双方降低与实现各自利益相关的成本和风险。”[47]伯蒂尔·杜奈尔(Bertil Dunér)也认为,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并非完全由施动方单方面的权力操纵,代理人在其中同样存在某种利益,双方都可以从代理人战争中获益,这方面的利益涉及权力以外的其他事物,它实际上必须被解释为某种共同利益(joint interest)或至少是利益契合(compatibility of interests)。[48]雅科夫·巴尔·希曼·托夫(Yaacov Bar Siman Tov)则指出,代理人是自愿的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正在被施动方利用,这两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利的,即使不是对称的。[49]对此,泰隆·格罗(Tyrone L.Groh)通过案例统计发现,在代理人战争中,具有当地语言知识和融入环境能力的行动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技能独自达成其目标,而缺乏这些技能的干预国即使能够实现其安全目标,但代价要高得多,于是双方共同行动可以提高实现目标的机会,并可能降低成本。[50]
第四,管控代理关系是一种双向权衡过程。丹尼尔·拜曼与萨拉·克雷普斯(Sarah E.Kreps)用“委托—代理”框架分析国家资助恐怖主义(State-Sponsored Terrorism)问题,这种代理关系的困境在于:国家有时希望保留外交政策自主权而决定不支持恐怖组织,是否愿意支持这些组织,将取决于直接军事行动的成本、合适的代理人以及监督效力。恐怖组织也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境地,虽然可以通过接受外部援助来显著增加自身的资源,但担心一时冲动使其受控于外部支持者,因此可能会选择保持自主性。[51]双方对自主性的权衡实际上构成了代理困境的一部分。艾迪·萨尔扬(Idean Salehyan)等学者将“委托—代理”框架引入内战暴乱问题研究中,作者认为外国对反叛组织的支持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代理”问题,这类代理人战争得以发生的条件是供需匹配:一个施动方[“供给侧”(supply-side),外部国家]必须向一个代理人[“需求侧”(demand-side),反叛组织]提供支持,后者必须接受这种支持。双方在此过程中处于一种双向权衡。特别是对于反叛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权衡就是如何获取外部援助又能保住自主性与国内合法性。因此,如果条件允许,强大的反叛组织更愿意依靠国内的支持来获得可靠的资源,而不是接受对其行为施加约束的外部援助。[52]这就意味着,在代理人战争中,更强大的或逐渐壮大的代理人更倾向独立自主地做决定而不愿意受到施动方的管控。
在阿莫斯·福克斯(Amos C.Fox)看来,管理代理关系的难题在于如何平衡施动方与代理人的自主利益与可承担的风险,这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对此,他进一步解释:代理关系基本内涵是施动方从代理人那里获取收益,代理人为施动方提供服务;共同的利益将双方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每一方都关注自主利益与可承受的风险;如果共同利益消失,或自主利益超过了共同利益,或需要承担的风险过高,那么代理关系将破裂(参见如下示意图)。[53]

(来源:Amos C.Fox绘制)
第五,代理损失主要与利益分歧、信息不对称有关。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委托—代理”框架来评估美国对当地伙伴的安全力量援助(Security Force Assistance,SFA)的效果,其中美国是施动方,接受安全力量援助的伙伴是代理人。安全力量援助旨在通过“赋能”(Empowering,包括安全训练、咨询和武器装备等)提高合作伙伴自身的作战能力来减少美军直接作战的需要,背后的逻辑是减少成本。但是,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和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这造成了“安全力量援助”出现系统的、固有的代理损失,因而也限制了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代理人军事能力的效果。对此,作者指出代理损失很大程度上跟利益分歧程度相关,正如代理理论所隐含的,代理损失与利益不一致的程度、监控和条件约束有关:“当美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更紧密一致时,我们可以期待每一美元的安全力量援助支出在合作伙伴的军事效率上有更大的改善。紧密的利益匹配、侵入式监督(intrusive monitoring)和可信的约束对美国的安全力量援助来说将是有利的。”[54]本杰明·卡奇(Benjamin Tkach)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美国(施动方)雇用的私人军事安保公司(代理人,PMSCs)的结构对2004—2007年伊拉克各省平民伤亡水平的影响。作者指出封闭的公司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困境,这带来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当美国无意中选择了可能追求自己利益的代理人时,就会发生逆向选择;如果私人军事安保公司对利润和美国对军事效能的优先顺序相互冲突,就会造成道德风险。基于伊拉克的案例实证发现,封闭的私人军事安保公司结构与平民伤亡存在较高的相关度。[55]
由于信息不对称困境的存在,代理人“租金”问题会造成持续的代理成本。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认为代理人战争是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一个“无止境”的博弈(an infinite-horizon game)过程:代理人也许是由于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处理问题。然而,这会带来后续的成本。当施动方需要付出代价才能让代理人解决问题并达成一个有效的结果时,承诺困境可能使代理人不会高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高效地解决问题,代理人的未来收益可能无法得以兑现。[56]罗伯特的研究实际上指出了代理人自主性难以被完全管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保住持续的代理收益,代理人有动机采取懈怠策略以延长施动方对它的需要。露西·霍维尔(Lucy Hovil)和埃里克·沃克(Eric Werker)也聚焦于这个问题,将外部力量资助暴乱组织针对平民的暴力视为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资助方的资金加剧了暴乱者对平民的暴力,暴乱者为了获得资金而选择对平民使用暴力,并努力使这个暴力过程延长、升级和被资助方所观察到(“暴力显示度”),以至于从后者那里获取可持续的援助。[57]毫无疑问,这种“无止境”的代理租金可能导致施动方掉进承诺陷阱,增加激励成本。
最后,管控代理人自主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伊莱·伯曼(Eli Berman)和大卫·莱克(David A.Lake)在他们主编的《代理人战争:通过当地代理人镇压暴力》一书中,运用“委托—代理”框架分析如何利用当地代理人来“减少扰乱”(minimizing disturbances)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们的关切点包括:如果施动方做得更少,它必须依靠当地代理人做得更多。那么,如何激励代理人去做施动方想做的事情?对施动方而言,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为原则成功地管理代理关系?对此,作者指出利益或目标的是否匹配是问题的首要维度,根据利益匹配差异来作出恰当的激励(奖惩)反应是管控代理人最主要手段。当施动方未能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时,当地代理人就会懈怠而不能按施动方的要求采取措施去抑制动乱。该书的作者们详细分析了发生在韩国、丹麦、哥伦比亚、黎巴嫩、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也门、伊拉克等地的10场代理人战争。通过案例研究,他们进一步提出三个发现:一是当施动方根据代理人的国内政治背景使用奖惩机制时,代理人通常会遵守;二是当动乱对施动方的显著性或代理人的努力成本增加时,施动方将以更强的激励(更大的奖励和惩罚)做出回应,代理人则以更大的努力达成预期;三是间接的激励控制不总是有效,或者只是部分执行了。[58]
与此同时,代理人自主性空间与代理关系模式存在关联。奥拉·舍克里(Ora Szekely)将代理模式引入代理人战争研究并与代理人自主性挂钩,这是他的创新之处。他认为在团结的单方委托(cohesive single principals)、分裂的集体委托(divided collective principals)和多边委托(multiple principals)三种不同的代理模式下,代理人拥有的自主性大小和反应不同,“施动方越碎片化,其代理人就越有可能被迫执行一项计划不周的政策,或者经历内部的分裂。相反,施动方越有凝聚力,其代理人的自主性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即使面对有凝聚力的施动方,在代理人内部在是否服从委托人的命令上也会产生分歧”。[59]为检验其理论假设,作者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进一步比较了叙利亚在不同年代作为集体委托人、单个委托人以及多方委托人与其非国家代理人的互动行为。
此外,限制性条件能更好地约束代理人行为。沃尔特·拉特维希(Walter C.LadwigⅢ)在其著作中讨论美国为什么难以依靠当地政府代理人来取得反暴乱的成功。在镇压暴乱的过程中,华盛顿与当地伙伴的关系往往很不和谐,华盛顿几乎无法塑造代理人的行为,几十年来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反暴乱援助努力。对此,他指出美国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支持处于内部崩溃危险中的弱小政权;另一方面,这些政权的继续生存高度依赖外部支持,而华盛顿对它们几乎没有控制或影响。他的研究表明,代理关系中的结构性紧张可以被视为冲突中“被遗忘的前线”(forgotten front),提供大量的援助却不会产生影响代理人行为的杠杆作用,而援助的限制性条件比无限的慷慨更有可能产生影响,即有条件的对外援助,才能更好地影响当地政府代理人的行为。[60]
(二)关于中东代理人战争的研究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东的代理人战争日益兴起,甚至“在当代国际冲突中占据主要位置”。[61]西亚北非动荡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进一步发生深刻剧变,原本脆弱的地区秩序分崩离析,域内外国家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环境。与此同时,部分脆弱国家的内部权力结构崩溃,不能完全垄断其领土边界范围内的统治,非国家地方行为体趁机而入,越来越有能力运用暴力手段和非对称策略制造长期的混乱。地区—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双重碎片化现象叠加显现,域内外干预国趁机与地方非国家行为体勾连,为代理人战争的频繁爆发创造了条件。从2011年至今,“代理人战争在中东地区获得了惊人的突出地位”。[62]既有研究已经对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回潮、演变和频发进行了讨论,为学界提供了独特的地区经验。
1.地区—国家双重权力碎片化
为什么在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下,代理人战争更容易爆发?21世纪初,美国大举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在中东地区进行长年累月大规模反恐战争,严重冲击了中东秩序。西亚北非动荡后,“中东地区秩序已从一个围绕并反对美国主导和管理的体系,转变为一个缺乏共同准则、外交渠道或平衡机制的多极体系”,中东地区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极化,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等强国加大在地区层面投射力量,试图重塑该体系以服务于自身利益,而美国既不愿也无力遏制地区多极化、无序化,撕裂了原本脆弱的地区安全架构。[63]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暴乱团体、地方武装、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趁机发展壮大,严重挑战了国家对领土的控制,破坏了主权规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东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致使代理人战争越来越多地与地区、国家权力碎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并渗透到“脆弱国家”的内部冲突。
首先,地区权力结构碎片化。地区权力结构与代理人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联,当一个地区陷入单极格局,霸权国对该地区的事务拥有绝对主导权,代理人战争在这种权力格局中没有任何着力点。当一个地区陷入两极格局,地区国家会严格地归化在两个阵营之下,对立双方达成均势状态,挤压了代理人战争滋生的余地。而当一个地区陷入多头博弈的碎片化权力格局下,任何国家试图主导地区事务的进程变得异常困难,而这将成为诱发代理人战争的有利环境。
回顾2001年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美国先是大举入侵、改造中东,后又从该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国力量的“大进大退”严重冲击了原有的中东权力结构,引发地区体系持续动荡、重组。受美国反恐战争、西亚北非动荡等典型事件影响,中东本已复杂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暴乱运动、恐怖主义活动、政权颠覆等乱象丛生,逐渐沦为多方力量角力的大棋局。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作为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玩家,纷纷通过扶植目标国代理人介入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脆弱国家”的内部冲突中。根本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力量希望借助地区代理人操纵中东地区发展进程和安全格局,进而谋取可持续的“结构性权力”。在外部力量加大政治操纵与战争资源输入的背景下,目标国的自主决策空间遭到压缩,不得不被裹挟进入代理人战争。
其次,国家权力结构碎片化。在中东的广泛冲突中,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需要跳出“国家中心”视角来理解中东代理人战争的爆发。一旦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碎片化,不受控制的内部各派势力便着手争夺最高权威。在安全困境的压力下,它们有足够的动机通过寻求外部援助和庇护来扩大力量优势,这成为推动代理人战争爆发的内在条件。当一个国家有能力行使最高主权并垄断全部暴力,其他行为体就难以对其造成根本性挑战,反之亦然。例如,刘中民教授研究了伊朗在中东发展代理人网络问题,指出对象国政权脆弱,无力控制国内局势并难以压制什叶派政治组织,是伊朗在该地区操作代理人策略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对此,他系统验证了伊朗与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海合会国家的什叶派组织之间的赞助—代理关系,最终发现伊朗在黎巴嫩获得了发展代理人策略的最佳环境,而在其他国家的表现则相对逊色。[64]
“9·11”事件以来,一些中东“脆弱国家”处于“权威缺位”状态,已经无法获得一些力量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尊重和服从,导致国家权力结构出现裂缝。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一些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只是保留了主权“外壳”,但它们没有中央政府(如索马里),或政府权威无法覆盖境内所有地区(如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65]“2019年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2019)报告显示,中东地区(包括阿富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和非洲地区[包括苏丹、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金)、南苏丹、索马里等国]是国家权力碎片化的高危集中区[66],这也是代理人战争频繁爆发的地区。“脆弱国家”更容易爆发代理人战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当局丧失最高权威,非国家行为体从权力碎片化的裂缝中找到生存发展空间,逐渐上升为国家政治以及冲突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中东地区,一些行动能力令人震惊的非国家行为体(如“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民主军”、“胡塞”武装、“基地”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依附于“脆弱国家”的权力割据状态,并与外部力量勾结,获取了丰富的作战资源,甚至能打败一些国家的正规军队。可以说,对于那些权力结构碎片化的国家而言,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是失去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被外部力量捕获,进而充当后者介入地方冲突的工具。因此,代理人战争的爆发“往往是国内力量难以被有效整合所致”。[67]
2.地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崛起
过去的研究往往在国家中心视角和美苏战略竞争框架下分析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常规力量在军事战略中的突出地位已得到充分理解,并在整个国防政策和规划中得到反映,但关于非常规力量的政策、资源和授权等方面的内容在国防文件中就不那么清晰。[68]显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Non-state Armed Actors,NSAAs)在冲突中的角色受到贬抑。中东地区广泛存在并能够实施国际行为的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它们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却能在区域内投射力量,对地区国家的主权构成挑战,深刻影响了中东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中东地区体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渗透性,催化了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反体系运动”。[69]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伺机崛起,导致中东地区安全形态呈现出“范式性转变”。[70]例如,“基地”组织以“本土化”的方式发展壮大,其控制的分支、团体与当地人、当地武装合作,通过建立当地政治联盟并获得部族领袖、游牧民族、农民和社区的支持来巩固其存在,这一战略使“基地”组织得以扩大其影响范围。[71]
面对非传统、非对称的威胁形态,外部干预国不断调整中东安全战略和作战方式,并逐渐转向扶植地方层面的非国家代理人,依赖后者“本土化”优势,以非对称方式应对非对称威胁。[72]“非国家代理武装通常被认为是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全部或部分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非正规军事组织,包括民兵、暴乱分子和恐怖分子”。[73]地方非国家武装的角色已经在代理人战争概念的界定中得以凸显,如泰隆·格罗认为,代理人战争是“一个干预国为参与武装冲突的当地行动者提供支持,以影响目标国的事务”。[74]克里斯·拉夫曼(Chris Loveman)则认为代理人战争是“一个国家为避免自己采取行动而利用另一个国家的地方暴乱集团或准国家组织与敌人作战,并向后者提供政治、军事和经济援助。”[75]
首先,中东非国家行为体崛起,改变了当地的冲突形态和战斗方式,驱动了外部干预国反思传统战争思维和战术手段的不足。相比于国家行为体,地方非国家武装对非对称斗争策略的理解更深刻。正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如果非国家行为体采取非常规的作战策略(如游击战)来反抗军事占领和本国政府,即选择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并在后者的掩护、支持下与正规军周旋,那么正规军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识别游击队和平民。如果正规军不能把二者分隔开来,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76]非国家武装深知作战能力的局限性,对与强国发生正面冲突毫无兴趣。同时,非国家武装也不相信国家正规军队愿意承受疲于奔波的折磨,或总是对低烈度、频繁的混乱作出及时反应。在当今的中东地区冲突中,非国家武装的作战思路是坚持灵活战术原则,进行相对分散的暴力袭击和小型战斗,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与国家行为体缠斗,试图在长期作战中持续消耗对手力量,进而增加国家行为体维持战争状态的成本和国内政治成本。[77]
中东地区非国家武装倾向通过恐怖活动、小规模扰乱、游击战、暴乱等非对称手段和策略来制造长期混乱,致使国家正规军“失灵”。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批评,“大战思维”在美军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军对非常规、非对称战争重视不够,事实也证明美军不善于应付类似“基地”组织“真主党”那样的非国家组织制造的小规模战争或暴乱。[78]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表示,“那些为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欢呼雀跃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善于发明创造的对手能够制造像恐怖主义这样的‘弱者的武器’”。[79]在肖恩·麦克法特(Sean McFate)看来,大国应对“持久混乱”状态的取胜方法有很多,并非所有方法都需要庞大的军队,因为“狡猾战胜蛮力”,先进的技术也不再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胜利,美国必须抛弃传统的战斗方式,将军队从传统力量改造为“后传统力量”,以新型的战略应对新形式冲突。[80]质言之,中东当地的“麻烦制造者”肆无忌惮地向国家发动非常规战争,制造了非对称威胁,而外部干预大国的反应往往显得笨拙而僵化。
其次,从实力和功能对比的角度看,代理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外部干预国试图改变传统作战思维和力量运用方式,转向强化和借助地方代理人的非对称优势,运用“以牙还牙”的策略来应对中东地方非国家武装制造的混乱。依赖地方非国家代理武装,对外部干预国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殊“优势”。
一是地方代理人具有合法身份的掩护。一般而言,外国干预者不太可能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而本地团体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能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和外部势力难以渗透的地区内运作,拥有外国力量永远无法做到的“柔性”方式融入当地社会的优势。例如,在叙利亚内战中,顾忌到当地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反弹,美国转向了代理人战略,扶植了“叙利亚民主军”(SDF),利用后者的合法身份在叙利亚东北部开展反恐行动。
二是地方代理人在处理地方性问题时更有天然的“专业”优势。地方代理人也能更好地利用本地关系网络、文化知识和语言、当地的相关政治人物和“线人”等资源优势,广泛获得情报,协助施动方更妥当地分配资源。[81]伊莱·伯尔曼(Eli Berman)等人明确指出,地方代理人具有特定的专业水平、较高的问题熟悉度和较低的事件处理成本,因而在解决“麻烦”方面具有天然的局部优势,而这种局部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代理方不具备这种优势,施动方将永远不会选择间接控制它。[82]
三是地方代理人的角色可以降低外部干预国在战争中的显示度。由于大规模直接干预中东国家的战争会遭到法律、财政上的合规程序审查,甚至涉及声势浩大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动员,那意味着干预国决策者要承担较大的国内和国际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面临诸多的阻力和风险。因此,外部干预国转向彰显当地代理人的角色,自身则隐退到合适的位置充当幕后主导者,降低参战显示度。例如,在中东的广泛冲突中,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域内外国家都试图避免投入自己的常规军力,但是它们之间的“影子战争”从未停止。
总之,中东地方性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改变了地区安全环境和冲突形态,它们运用非对称的方式挑战国家行为体主导的秩序,甚至成为地区行动的强者。域内外干预国逐渐重视和依赖地方性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并将后者扶植为代理人,这是构成代理人战争的一个要素。
3.内外力量勾结
双重权力碎片化为内外力量勾连提供了机会,这是代理人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中东地区与国家双重权力碎片化,为外部干预方和国家内部力量提供了利益交换的“市场”环境,其中前者可以方便地物色到愿意接受其援助和影响的地方代理人,赋予它们资源和能力,唆使其破坏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而后者可以通过让渡全部或部分自主权来获得外部庇护和赋能。
在过去二十年,绝大多数暴力冲突“来源于失败的国家内部,而非国家之间”,而且“多数情况下,内战都会涉及境外势力的介入”。[83]自1945年以来,在285个反叛组织中,有134个得到了外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另有30个组织被指控获得外国支持。[84]质言之,国家政治权威的碎片化与外部力量的渗透交互影响,共同致使“脆弱国家”滋生广泛的地方性暴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暴力,并逐渐演化为代理人战争。这种现象在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伊拉克等中东“脆弱国家”比较常见。
当内外利益交换匹配时,代理人战争爆发的条件就更成熟。对于外部干预国而言,把风险和代价转移给目标国代理人而不必在现场处理问题是一种极具诱惑的策略。但外部干预方必须物色到一个似乎愿意充当代理人的地方团体,并且在为其利益采取行动时,这种诱人的前景才会出现。[85]如果仅存在强大的外部干预方,而目标国的权力结构十分完整,这种情形则不利于内外勾结,也难以推动代理人战争的爆发。例如,美国资深外交官埃里克·爱德曼(Eric Steven Edelman)从近年来伊朗国内局势的变化中敏锐地发现一丝裂痕,因而产生了利用内部代理人去颠覆伊朗政权的大胆设想,即美国需要一个“升级版的秘密行动计划”,来协助伊朗国内反对派削弱和颠覆伊朗的神权政体。[86]然而,就目前而言伊朗国内并没有冒出值得重视、可供利用的反叛组织,因而美国推动伊朗内部爆发代理人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
当今中东地区的大多数代理人战争呈现出“外部干预国+地方非政府武装力量”的组合形式。中东地区是双重权力碎片化的重灾区,在这种情形下,外部力量得以向动乱国家渗透,并轻易地将目标国反对派或地方力量“捕获”为代理人。[87]而目标国内部各派力量为了在相互竞争中胜出,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外部力量的工具。如此一来,中东地区“内外联动”型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外部力量通过干预给分裂势力足够支持,原来的主权国家将不得不面临碎片化的结局”,“内生性的安全规范缺失、外源性的对中东安全秩序的干预,以及内外安全困局互动性牵制”,其“本质上是外部干预和中东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反映”。[88]
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爆发,美国领导的北约国家趁机支持反对派暴乱武装,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然而,围绕利比亚的战后政治秩序重建却很快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代理人内战。2014年夏天以来,由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和其他国家支持的独裁军阀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对联合国承认的的黎波里政府发起了进攻,后者又得到了美国、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支持。2016年10月,《德国之声》发表题为《卡扎菲被推翻5年后的利比亚》一文,文中指出:“随着卡扎菲的被推翻,人们希望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和开放的利比亚社会。然而这一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恰恰相反:国家陷入混乱,没有有效的政府。与此同时,多个政府争夺统治权,全国有数百个武装组织。”[89]2022年8月底,的黎波里爆发血腥冲突,造成30多人死亡。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德贝巴(Abdulhamid Dbeibah)指出,这是利比亚内外势力共同策划的结果。
总之,中东地区秩序和国家结构的双重“碎片化”,为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创造了环境。在地区体系层次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主导中东秩序,相反,地区强国和域外大国之间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展开激烈的博弈,撕碎了地区体系,中东秩序异常脆弱和紧张,表现出长期的权力真空和缺乏稳固的政治身份;在国家层次上,一些中东国家的中央政府受到非国家地方行为体的挑战,没有能力恢复完整统治,碎片化的政治安全环境为内外力量的勾连创造了空隙。与此同时,目标国内部地方行为体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和安全竞争优势,主动或被动投靠外部力量,成为后者操纵的工具。地区与国内两个层次的权力碎片化叠加,为外部干预国与地方非国家行为体的勾结创造了条件,加剧了中东的冲突向代理人战争的演化。
(三)关于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行动,但很少直接参与该地区的冲突。除了1958年和1983年对黎巴嫩的干预,1991年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更愿意在该地区扮演一个间接的角色,为当地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经济、武器和情报等方面的援助。可以说,美国对中东的直接干预是例外行为,而通过代理人战争对该地区施加间接干预则是更常见的现象。“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大举入侵、改造中东,在中东开展反恐战争,引发地区体系持续动荡、重组。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冲击波接踵而至,中东本已脆弱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恐怖主义、极端暴力、教派冲突、暴乱、内战等乱象叠加丛生,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脆弱国家”逐渐陷入“多边影子战争”(multisided shadow wars)的泥潭。[90]
1.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背景
从2001年开始,美国在中东卷入持久的军事冲突,消耗巨大但是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限制了美国的中东霸权。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其经济实力遭到重创,不得不推进中东战略收缩,试图摆脱“永久战争”(forever wars)困境,以聚焦美国内部议题。与此同时,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不得不重新分配战略资源,重返大国竞争轨道,以维护其关键利益。美国大举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并没有为中东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也没有促使该地区形成美国所期待的秩序。这足以证明,美国试图以常规军事力量改造中东的构想难以成功。近十年来,美国试图通过中东战略收缩来挽救其霸权衰落,并将战略重心和资源转向亚太。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放弃利用大规模常规战争塑造中东秩序,降低维持中东霸权的成本。随着美国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大规模、军队密集型(troop-intensive)的战争,“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资源转移到间接的、隐蔽的、看似廉价的手段上,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91]从小布什政府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清楚,向中东地区派遣大规模美军地面部队来维护美国的中东霸权,只会使自身长期陷入持久消耗战的泥潭,而这种做法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这三届美国政府在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努力平衡美国在中东地区扩大的安全目标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92]奥巴马上台后,“中东问题在他的议程上并不是很重要。整顿美国的财政状况,重振美国的长期经济实力一直是奥巴马的首要任务。从一开始,奥巴马就把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他和他的助手们相信美国的未来所在的太平洋和亚洲”。[93]奥巴马调整小布什政府中东霸权政策,放弃大规模军事干预的主要原因包括:中东舆论的觉醒、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地区大国的出现、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和战争的高昂代价等。
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逐渐转向借助当地伙伴力量帮助美国维护战略利益,试图以间接介入方式代替大规模地面军事卷入。“从2011年开始,美国中东政策进入新阶段,其政策介于离岸平衡与大规模直接介入之间,可以称之为‘空中干预’时代”。[94]特朗普政府信奉“美国第一”的理念,并热衷于大国竞争,因此更加不愿意在中东地区投入大规模军力。2020年6月,特朗普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重申了其军力运用逻辑:美军不是去重建其他国家,不是去解决遥远地方的古老冲突,不是当世界警察,而应该结束“永久战争”,集中精力守卫美国的核心利益。[95]实际上,特朗普在上台后延续了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坚定地推动美国摆脱中东陷阱。[96]由此美国进一步加快从叙利亚、阿富汗的撤军步伐,并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
为挽救美国中东霸权,依赖当地代理人日益成为美国解决中东麻烦的“折中”方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进大退”搅动了该地区权力结构,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趁机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而美国对中东秩序的主导能力则相对下降。为应对中东战略收缩“后遗症”,挽回在中东的巨额“沉没成本”(sunk cost),美国既难以一走了之,但又不具备大规模重返的条件。在进退失据的困局中,美国转向“轻足迹”(Light Footprint)、“幕后领导”(Lead from Behind)和“由、与、通过”(By,With,and Through,BTW)策略,妄图扶植中东地方代理人,以更低的成本和显示度维系其中东霸权。
代理人战争逐渐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U.S.Central Command)实现中东战略转型的工具。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BTW策略适用于中东地区环境,扶植、依赖中东当地代理人是可行的方案。“困扰中央司令部的军事问题是多方面的。从在责任区域内打击‘伊斯兰国’,到在阿富汗牵制塔利班,这些问题跨越了责任区域的地理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已经决心通过有限责任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这意味着他们不把美国军事人员放在这些战斗的前线,而是选择通过代理人行动。”[97]中东地区已成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试验场”,主要涉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脆弱国家”(见表1)。
表1 美国介入中东代理人战争统计

续表

2.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成效
美国在中东运作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其战略收缩和地区政策调整的一部分。美国这么做会促进其目标的实现吗?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基于施动方“受益”的逻辑,安格斯·李(Angus Lee)指出,“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采用代理人战争作为主要战略具有诱人的前景”,它允许美国在中东继续投射力量,在帮助地区盟友作战方面享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美国绕开财政预算、人员伤亡等因素构成的障碍,为美国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另一种方式,“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干预可能是美国硬实力的局限性与其目标之间的必要妥协”,但从长期来看,即使失去完全控制权,美国的回报也可能会更大。[98]
安德烈亚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指出,由于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和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美国面临战争疲劳、军费和军队缩减问题,因此将作战任务外包给地方代理人成为保护美国利益的重要手段,这是“风险转移”政策。[99]有美国学者建议应将代理人战争作为“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的组成部分,即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卸责任与建立均势等手段向合作伙伴转移资源和负担,进而达到远距离遏制对手的目的。[100]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幕后领导”策略是成功的。奥巴马政府倾向发动留下“轻微足迹”、脱离公众“雷达”(off the public radar)和富有成效的代理人战争。[101]这一方式就被白宫顾问称为“幕后领导”,其“核心思想是授权其他参与者听从命令”,将风险转移给代理人和盟友,而自己则脱离“事发现场”,通过后者的努力来促进美国自身利益最大化。[102]
此外,学界注意到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地方化”成效。人们对代理人战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将其视为美苏冷战对抗的产物,这是对代理人战争一种过时的、刻板的印象。在不断演化的战争形态中,“代理人战争实际上是用来处理当地人关心的地方层面事务”。[103]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教训促使美国重新调整了镇压暴乱的方向,即不直接使用美军介入其中,而是通过经济和安全援助及作战建议,重点支持地方力量的反暴乱努力。[104]例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国依赖库尔德武装打击恐怖主义,利用地方部落来应对“基地”组织制造的麻烦。实际上,历届美国政府不仅在地方安全机制约束下开展工作,同时也拼凑一些辅助的、非正规力量,来填补在地作战的能力缺口。[105]西约姆·布朗指出:“美国从海外军事战斗转向推动区域和平与安全或国家建设,而大部分角色转移到了地方代理人。”[106]概言之,美国倾向将中东的地方性麻烦交给地方代理人解决,以增强其应对非对称威胁的灵活度和有效性。
相对于上述的积极看法,亚历山德拉·斯塔克(Alexandra Stark)的研究表明,美国在中东进行代理战争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甚至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在代理人战争中取得快速、彻底的胜利,而是发现自己陷入了复杂的泥潭,地区施动方已经把局部冲突蔓延到国界之外并变成了破坏稳定的地区战争。[107]此外,亚历山德拉·斯塔克和阿里尔·阿拉姆(Ariel I.Ahram)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美国应该脱离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因为“代理人战争往往是漫长而难以取胜的,这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失望,他们期望以廉价而简单的方式解决地区安全挑战。但是施动方和代理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委托—代理问题。施动方必须冷酷无情,关键是让代理人为其目标战斗和牺牲。反过来,代理人试图操纵施动方,使后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投入更多资源,同时追求自己更狭隘的议程”。[108]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武器并没有被全部用来打击恐怖组织,有些流入“努斯拉阵线”手中。[109]美国律师协会人权中心副主任布列塔尼·贝诺维茨(Brittany Benowitz)等人对美国在中东运作代理人战争也持消极看法。他们指出,美国越来越依赖间接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支持非国家武装代理人增加了暴行的风险,因为有外国支持的武装团体不太可能依赖当地居民的支持,导致它们更有可能掠夺、恐吓平民,这些行为是非法的,反过来又可能增加美国的连带责任和援助风险。[110]
(四)对既有研究的总体评价
既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笔者对代理人战争一般规律、理论的认识,有助于笔者以更平衡的视角观察代理关系中的张力,并意识到管控代理人自主性问题是代理人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与此同时,既有研究对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实践特点、效果进行了总结,为笔者提供了具象的经验素材,进一步强化了笔者的问题意识,即美国的中东代理人战争管控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可以说,既有研究已经构成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研究“全景图”的重要一部分。
1.从“施动方中心”到双向博弈
既有研究从一般理论、地区经验和美国的具体案例等维度增进了人们对代理人战争的认识,笔者从中提炼出以下观点。
一是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施动方中心”论范式,而代理人的自主性和利益并没有被放到研究视野的显著位置,因此有必要尝试在方法上以更平衡视角观察代理人在代理人战争所扮演的角色。
二是既有研究已经对代理人战争被理想化、简单化、片面化的描述表达了不满,认识到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执行”模式,而是难以控制的双向博弈,代理关系中的持续张力增加了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
三是既有研究已尝试引入“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来观察代理人战争,这有助于纠正“施动方中心”的叙事方式。随着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以及代理人战争的“成本—收益”进入研究视野,代理人战争的固有软肋被暴露出来。
四是施动方在管控代理人战争走向和代理关系的过程中面临系统性挑战。施动方与代理人的共同利益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所拥有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与此同时,施动方为管控代理人而施加必要的激励与监督,但这些“纠正”举措并不能彻底消除施动方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和背叛。
2.代理人战争性质与概念分歧
通过上文的梳理发现,学界对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和概念尚未达成高度一致。在不同的文献中,学界对代理人战争的界定至少有十几种,且人们对代理人战争相关名称的表述显得多元且随意,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地步(见表2)。
表2 代理人战争相关表述

表述上的混乱反映出人们对代理人战争性质和概念存在分歧,也意味着学界对代理人战争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足。长期以来,学界基本上也承认代理战争是“概念化和理论化不足的”(under-conceptualised and under-theorised)。[111]对此,布列塔尼·贝诺维茨(Brittany Benowitz)、汤米·罗斯(Tommy Ross)给出如下评价:
一些评论家倾向用“间接”(indirect)、“替身战”(surrogacy warfare),或“由、与、通过”(by,with,and through,BTW)等术语描述代理人战争,这些术语上的差异部分源于对代理人战争确切性质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这一术语意味着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施动方对其代理人的行为施加实质性控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包括一种更广泛的关系,其中一方支持另一方参与敌对行动。然而,在实践中,施动方很少对代理行为施加实质性控制。相反,代理人几乎总是根据自己独特的利益、领导特质和内部压力来运作。[112]
很显然,贝诺维茨和罗斯不满学界对代理人战争的描述停留在刻板的“主从”形式上。实践中的代理人战争远非如此,当代理人的自主角色被纳入其中,人们看到的将是另外的面貌。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未能深入考察施动方和代理人之间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和交互博弈,而这是影响美国运作中东的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因素。随着研究的推进,侧重“施动方中心”的研究范式在概念、逻辑上和经验上逐渐遭到挑战,代理人自主角色“再发现”的过程和意义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学界逐渐深化对代理人战争复杂性的理解,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管控代理人自主性的难度、成本并开始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此外,略有不足的是,国际关系学界在管控代理人自主性这个问题上尚没有形成较高的关注度和共识,自然也没有构建理论化程度较高和更加普适性系统分析框架。更直接地说,既有研究仍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观察视角较为零散且学界缺乏足够的理论对话和积累,不利于形成广为接受的研究脉络、规范和共同体知识。因而,这也显示出在代理人战争研究中有待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和可能性。